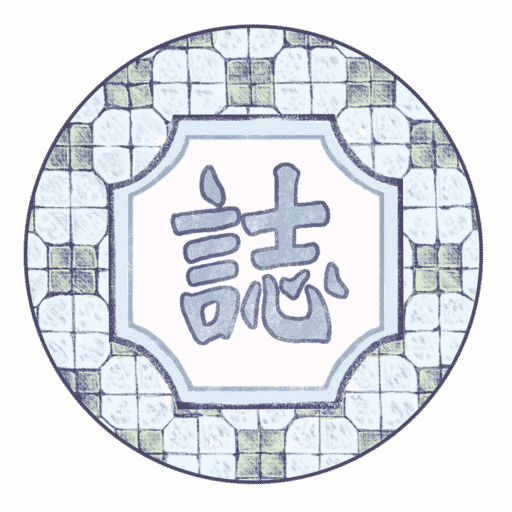1/ 55
2020年,一場世紀瘟疫改變了世界的秩序。限聚令下,香港抗爭冷卻,社會氣氛低沉。很多人今年過得渾沌、灰暗而平淡,甚至不願回想2020年。 加入社運八年的黃子悅就在一年之間,經歷高山低谷。 今年她參加民主派立法會初選報捷,但特首一聲令下就將選舉押後,未來還不知有沒有選舉。一轉眼,眼前一切幻滅,停下來,壓力便湧至:案件程序、前途、財政、生活大小事;又眼看著戰友們一個一個被判入獄⋯⋯。 2020年,她疲憊不堪。現在她只想好好休息,重整人生。
這一年,香港人的記憶被無力感與絕望佔據,她希望大家好好保重:
「唯有撐住,這段時間很難過,但只有生存下去才有機會改變,否則你甚麼都改變不了。」
「我最想當然是去旅行!」
黃子悅的新年願望,未必能夠達成。 去年十一月「營救理大」示威行動中,她被警方拘捕,並遭落案起訴暴動罪。事發至今超過一年,案件仍未開審,她預料審訊要到2022年才展開。 她被沒收旅遊證件,不准離港,要守宵禁令、禁足油麻地一帶、每星期報到一次。去年八月,她和家人去了土耳其,「結果就去了最後一次旅行。那次去了一個星期,不斷看新聞,今天誰被捕、哪裡有衝突,不太開心。」 這一年來,她活在嚴苛的保釋條件下,生活受到很多掣肘。不過,她覺得自己比別人幸運。「其他手足更慘,我只是夜晚十一點開始宵禁,有些手足可能夜晚七點就開始。我就會想,算吧,沒有甚麼好怨,我不是最慘那一個。」她的生活其實是很多被捕人士的寫照。
初選勝出 取消選舉的落魄
黃子悅去年被捕後,花了三個月調整心態,然後她背著暴動罪參加民主派立法會初選。
「如果甚麼都不做,其實都是等入獄,倒不如試一試,將自己的身份提高一點,延續抗爭能量,不要浪費了自己。」
她在新界西初選中,獲超過二萬票以第三名出線,拋離一眾泛民前輩。這是她今年攀上的一座高峰。
黃子悅說,參加初選是今年最重要的決定,因為參選之後,知名度提升,變相有更大責任,心態也改變了:「別人對你有期望,更加沒有理由放棄。」 然而她很快便從高峰墜落。她宣佈參加立法會直選之後,選舉主任裁定十二位參選人的提名無效,而黃子悅在等候確認提名期間,政府就以防疫為由,押後選舉一年。 她突然從繃緊的選舉工程中釋放,猶如墮入深淵。
「突然間放鬆了,不知道下一步要怎樣。再加上現實問題:本身只差一年就畢業;然後面對暴動案,開始收到不同的證據,很多程序要處理,自己又要面對財政和生活各種事項。很累、很沮喪。」
抗爭冷卻 一年彷如隔世
這半年,黃子悅從鎂光燈中退下,由候選人變回學生,平時除了幫忙擺街站,便是專心讀書。她說,自己的精神和身體也需要時間復元,再重新整理自己的人生。 步伐放慢,壓力即迎面撲來,令黃子悅感到焦慮。她不打算再參選,亦不想從政,因此知名度成為她的負累,讀藝術的她,擔心畢業等於失業。「其實就算知名度不高,但你曾經被捕,老闆可能會看新聞,或上網搜尋一下,就發現你曾經被捕,手足找工作都會有一定難度。」
她也想過進修,但擔心讀了半年就被判入獄,變相失去學位。 一年之隔,彷如隔世。疫情肆虐、街頭抗爭冷卻,港區國安法生效,十二港人被大陸關押,歸來無期。每個清晨,香港人都害怕看新聞報道誰人被捕,或誰人被判入獄。 黃子悅覺得,今年有明顯的絕望感,連新聞都不想看。每當看見有人被捕,她都會問自己可以做甚麼。「我最多只能發個文章,用自己的影響力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然後呢?被捕的人還是繼續被捕,被控要坐幾年十年的。」 「好絕望,甚麼都不想做,我逼自己也做不到。唯有等,等時間過去,令自己好一點。」
在等待審訊期間,她看著自己的朋友、選舉義工,昔日學民思潮的戰友,一個一個被關進囚牢。「你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叫自己撐住。」她說。 黃子悅坦言,就算自己能預測政權會有甚麼打壓,都沒有能力和方法應對。難道只能坐以待斃?她說,現在最重要是照顧身心。「無論是抗爭者還是普通人,都總會覺得自己做得不夠。當看見身邊的人,每一天都面對不同打壓。
這一刻不照顧好自己,同時會令其他人更辛苦。」她希望,香港人都能先照料自己,想清楚下一步,無須因對被捕者內疚而急著去「贖罪」。
她從開始已經想過,無論自己多麼投入,民情終有一天會冷卻,但她深信這不是終結,而是抗爭的必然進程。「唯有撐住,這段時間很難過,但只有生存下去,才有機會改變,否則你甚麼都改變不了。」只要還活著,就有很多事可以期待,她認為現在要好好將抗爭記憶傳承下去,勿因事小而不為。
來年有咩願望?「想去旅行」,官司纏身,去旅行成為黃子悅奢侈的盼望。

覺醒同喜同悲 歡笑多於唏噓
她最近很少看社交平台,因害怕看見別人快樂地生活,這並非出於責怪,而是羨慕。「突然間會有一刻很羨慕,為甚麼我要過成這樣,為甚麼他們那麼開心,為甚麼我要等入獄,害怕甚麼時候要被捕。
為甚麼別人有這種生活,有時真的會羨慕……。」 覺醒是痛苦的開端,眼睛睜開那一剎,見盡世間瘡痍。主權移交之後,本地抗爭成功的例子很少。對於黃子悅來說,參與社運八年,痛苦居多,唯一的快樂是來自同路人的扶持。
「大家在同一個地方,做同一件事,感覺就像他們跟你有緊密關係,好像家人一樣,那種感覺我還記得。」 去年「反送中運動」期間,抗爭者之間的感覺、共同關係,是她理想中的香港——藉著共同苦難,互相理解,就算沒有相同經歷,也會選擇支持對方;面對不公義時,不會盲目包容,反而會指正,令事情變好。
每當感覺失落,她便會想一想,當初自己接觸過、相遇過的人,他們今天過得怎樣。或許是一廂情願,但她依然相信,曾經在她身旁的每一位抗爭者,都沒有拋棄她。
「現在我是半休息狀態,可能他們也會覺得很累,面對同樣的痛苦,比起怪責,我會覺得既然你覺得疲倦,那就要好好照顧自己,到有足夠能量再出來。」
反叛、擇善固執

1/55
黃子悅雙手有對紋身,一邊紋著歌詞「MUSIC IS THE HOME FOR YOUR PAIN.」;一邊紋上一個吹長號的女生。中學時,她很喜歡音樂,會吹長號。直至參與社運之後,她才開始少碰樂器。
她剛滿十八歲,就有第一個紋身:「我有點反叛,覺得圖案漂亮,紋在身上好看,所以就紋,沒有特別原因,也沒有想太久,純粹覺得紋了之後不會後悔,那便紋了。幸好現在也沒有後悔。」黃子悅很怕痛,紋身的時候,她時常亂動,令紋身師很難下手。但因為反叛,愈痛她愈要去做。 乖乖讀書、考試、讀大學,然後工作,是典型香港人生涯。然而「反叛」的性格,帶她踏進社運,拒絕了一條循規蹈矩的道路。 2012年,政府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掀起大型「反國教」運動,學民思潮在當時成立,最後暫時拉倒了國教科。那年,讀中四的黃子悅加入學民思潮,參與「反國教」運動,開始投入社運。2014年雨傘運動,她絕食超過一百小時。
2015年,她當上學民思潮發言人,直至一年後學民思潮解散,她成立教育實驗學社,到今年離開。 她對公義、扶助弱勢有一份執著。她說,就算這刻覺得累了,過一段時間又會忍不住做些事。「我想成為一個看見別人受苦難時,願意做些事的人。就算當初我沒有加入學民,怎樣迂迴曲折,最後都是走相近的路。」她說。
社運路上,家人成為黃子悅的後盾。「有些手足可能跟家人翻了臉,無家可歸,斷絕來往。我很幸運,家人無論怎樣都支持我。就算他們未必同意我做的事,但他們一定愛我,有需要的時候他們永遠都在。」 她想過,換轉是別人,循規蹈矩的話,二十三歲可能已經畢業開始工作,可以給家人家用。
相反,自己曾休學一年,如今更身負暴動罪,前途未卜,因此對家人感到抱歉。「但我想繼續堅持,唯有盡量平時對他們好一點,別讓他們擔心。照顧好自己,不要常常生病。」
「慶幸自己沒有跟隨那條循規蹈矩的道路,過毫無意義的人生,慶幸那刻反叛了一下,無悔的。」
這種反叛,可能是擇善固執。
三年前,傘後抗爭低潮期,黃子悅自己一人跑到台灣旅遊。那時她去紋身,紋了一個「揸緊中指」手勢在自己的背上。抗爭失意、人生迷失,她希望提醒自己,做人要捉緊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