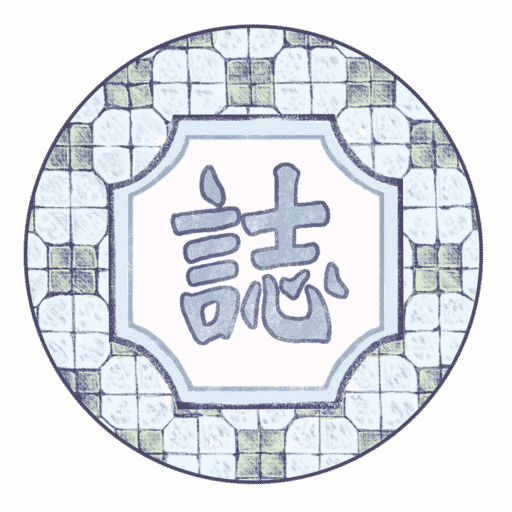一月六日清晨,愛狗波波的叫吠聲,劃破靜肅的夜空。
「是警察嗎?」岑敖暉(Lester)睡眼惺忪的問自己。
「隆、隆、隆!」有人拍打鐵閘。
當時還是女友余思朗(Nicole),下樓看過究竟。「噢,終於要來了。」她那時內心怔了一下,冷靜應對着。不久,幾隻厚厚的靴子就踏進他們的家門,把她心愛的潔白地氈踩得髒亂。
那天,警方在各區,以涉嫌違反港版《國安法》的「顛覆國家政權」的名義,逮捕了55位參與2020年7月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初選的人士,岑敖暉是五十五份之一。「參加初選是顛覆國家政權?哈,荒謬成咁?」這個念頭一直在他的腦海盤旋。
在被拘留的三十八小時,他說了幾百次「我無嘢講」;吃了一個極難吃的腸蛋頹飯;睡了一頓很漫長的覺——他形容,用兩張毛氈摺疊成枕頭,再用三張毛氈包裹着,讓身體有種暫借的溫暖。
一月七日,晚上接近九時,他徐徐步出西區警署,獲准保釋。
一月九日,他打電話給律師,劈頭第一句就是:「畀單靚case你接⋯⋯,我們要結婚了。」

是經歷了怎樣的苦難或期盼,讓二人篤定彼此,如他們結婚誓詞所述,「在苦困中仍然擁抱彼此,日月流轉,惟矢志不渝」?
「未來要一起過。」Lester的聲音帶點沙啞 ,卻不乏溫柔。語畢,眼光落在Nicole身上。
剛剛獲得消息,二月二十八日,Lester需要提早到西區警署報到,估計將正式落案起訴,可否保釋,並不樂觀。他們都知道前路命途多舛。然而,在最不能談未來的人身上,她看見未來,他堅信要一起過。
認真

近來社運圈內確實不少人趕快結婚。最直接的想法難免是,牢獄攤在面前,若果對方「名正言順」,探監的權利將會大大獲得保障。是因為這樣,讓Lester和Nicole萌生結婚的念頭嗎?
「我們最壞的打算是,如果被送中,是太太還是女朋友的分別確實好大,因為一直有跟開12港人個案,有些女朋友的情況好坎坷,深深明白直系親屬擁有的權利比較多。」他形容,名份下的功能性,確實佔思考結婚的其中一個部分,但這絕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我反而唔想因為咁樣而結婚。」Lester手裏拿着一個啤酒罐,捏緊了一下;Nicole坐在不遠處,左手托着腮、右手撫摸着貓兒,傾聽着新婚丈夫的理論。
「我諗嘅係,(遇到一個人)係就係,唔係就唔係。唔係覺得可以承諾的,就唔好耽誤人哋(別人),無咁多時間去浪費(沒有這麼多時間浪費)。」他形容,當處境殺到面前,面對和經營關係,都是用上前所未有的目光,逐格逐格檢視生活上每個細節,他的嘴裏連續碎碎着:「生活,要認真過、要認真過、要認真過。」重要的事情他說了三次,高牆再高,擋得住用身,卻擋不住那份認真,兩人奔向對方的勇氣,在一月六日後,更是澄明。
「我覺得,面對極權,可以做『渣男』嘅空間都少了好多。」
語畢,兩人對望,捧腹大笑。
「如果太平盛世,可能仲可以『渣一下』。」Lester續說。
「好可惜呀嘛?」Nicole用腳端了他一下。
「好可惜。」Lester笑着回敬。
那,轉過去問問Nicole,有沒有人提醒過你,做Lester的另一半風險會很大、這個婚真的要結嗎?「一定有,一定有,好多人都咁講。」她坦率地說。
但是轉念一想,她覺得被極權騷擾生活上每個細節,以致拍不拍拖 / 結不結婚 / 和誰結婚都要受影響,她覺得「條氣好唔順」:「如果要計算『so called有無將來』,咁日日都有人被拉或被判刑,那好多人都看似無將來,如果個個都咁諗,香港死梗。」她認為,無論行動還是心態上,都要去抵抗極權這種入血入骨的騷擾,雖然好艱難,但盡量不被影響每個做的決定,她說時,一臉倔強。
「所以說,從這個角度來說,我是被物化了,我是你用來達成自己抵抗極權慾望的工具。」Lester忽爾搶白。
「 黐線!」Nicole沒好氣回應。
「你這『渣男』仲話我,你喺極權下繼續做到個渣男。」Nicole再反擊道。
兩人並肩坐在沙發上,甚麼都端出來討論、辯論,凡事愈辯愈明,不要將問題掃入沙發底,這是他們最直接、坦誠、磊落的相處方式。

離慾
一月二十五日,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他穿着卡其色西裝外套,她披了一襲長長的蕾絲白裙,在一眾親友的祝福面對,結成夫婦。
宣讀誓詞前,律師說笑外面有保安(警察),Lester嚇得一臉心慌意亂。幸好成婚一切順利,有見證者更說,可以參加這場喜事沖沖喜,是整個一月最值得開心的事。
一場婚禮,本來想低調處理,卻彷彿被添上一層公共意義;本來愁雲慘霧的臉容,生出別有神采的燦爛和絢麗。「我不是想這樣quote,但這樣有點像試一種抵抗極權的方式,我們唔衰得。」Lester回想道。「這樣侷住唔衰得,都是好的,是一種力量。」Nicole和應他。
在風雨如晦的日子,兩人抱得更緊,眼神不離也不棄。以後的日子,只要兩人互相扶持,大概比一人容易過?Lester卻斷然搖頭。
他說了一個故事。自從去年開始,他總是維持着探監的習慣,一星期有兩天去羅湖懲教所,兩天去赤柱監獄,和因反送中運動入獄或還押的人,建立了一些關係,想那些人感受得到,他們並沒有被遺下。
有天探監,他探的手足告訴他,「如果六月時審完被定罪,我就會和女朋友分手。」他當刻,立即痛罵他:「吓,你做乜幫人揀?分唔分手你應該讓她自己選擇。」那時,手足覆了他一句:「我想可以自由地坐監。」
Lester聽罷,立即明白起來,「如果他心裏帶着一個人坐監,永遠也帶着了。有牽有掛是一個負擔。」他形容,有人一起前行當然好,但離慾是最難處理的部分,他頓了一頓,靜默了良久,才緩緩吐出如縷輕煙的幾句話:「如果無另一半,簡單來說,nothing to lose。我依家係have something to lose,某程度上,難咗,痛苦咗好多,但雖然痛苦,仍然要做。」
環境惡劣、食物差、甚至勞動異化,Lester並不特別懼怕或擔憂,「到時會寫信、睇書、做運動,intellectual上更加強大了。」但是人心由肉造,要與太太、愛狗、愛貓(他稱之為仔仔女女)暫時分隔,是他面對囹圄最艱難的課題。
刑期
二月十日,年廿九的下午,Lester首次到警署報到,順利續保。
早一天,他提前和母親吃團年飯。席間,他們沒多說甚麼送別的話、沒流過半滴眼淚。他用理性說服媽媽,當天應該是能夠保釋的,母親因而沒有多說幾句。

他突然回想起,一月六日被捕當天,母親特地去了他的荃灣議員辦事處,為了等待警察來搜查時、匆匆見上兒子一面。「她那時是怎樣的?」Lester這才問回,當時陪在他母親身邊的太太。「她好冷靜、好calm,睇完就咁話返屋企了。」
2014年佔旺清場期間,Lester被指違反禁制令而被控藐視法庭。他很記得,當時判刑前夕吃晚飯,母親哭成淚人,他直言,最怕這種場面,重覆上演。
她有勸過你離開嗎?「沒有,佢知我點諗、脾性係點。」Lester堅定地說。
他形容,母親現在會用些較委婉的方法,嘗試探他的口風:「例如她會問我,阿聰呢排點呀?係咪都過得可以呀?有無諗過離開?會唔會更加好?」Lester不認同,試着跟她解釋,他已經決定留下來:「走不走,either way都是不好,都是非常不好,這是我們一代人要面對的,沒辦法。」
誠然,他觀察到,母親的接受程度,其實進化了很多:「佢依家會覺得,有個刑期都係『好事』,『坐幾年』是可以接受的range,佢只係怕無刑期⋯⋯」然而,當刑期真的具體成了時鐘上的分秒針,也化成了無盡的等待和缺席,又是不是那麼可以接受呢?
砥礪前行

訪問於新年期間進行,兩人在餐桌前懶洋洋地捉着圍棋,櫃門上當眼處,黏着三張揮春,最左面洋洋灑灑的毛筆字,是「砥礪前行」。當談到入獄等於漫長的離別與等待,他們不約而同指着那手字。
「他寫的。」Nicole說。
「我好喜歡這個詞語,佢唔保證你一定行到、一定有進展,但係有這個過程,如在在磨刀石上磨,行前少少、退後少少、又再行前。」Lester解釋道。
「所以無嘅,煮到埋黎就食。唔食就等於認輸。」Lester續說。
「唔輸得嘛。」Nicole接口。
「驚就實驚,恐懼、負面情緒一定有。」Lester坦蕩地說。他眼尾瞄一瞄Nicole。「我唔覺得佢會搞得惦。」Nicole:「我都唔覺得我會搞得惦。」
Lester重覆同一句話:「我都唔覺得我會搞得惦,但係⋯⋯」
「咁都要㗎啦,有得揀咩依家?」Nicole接上了未說完的句子。看着兩口子互相搭嘴的默契,旁人感到一陣暖流。「有時唔輸得,都係一種能力。」Nicole又是一臉倔強。
「我對佢有信心。」Lester眨眨眼,他的目光,最後落在櫃門最右邊的揮春,寫着「愛你一萬年」。
不論二月二十八日的控罪如何;不論入獄與否;不論區議員席位會否遭到DQ;不論制度之路是否將盡;他信守的承諾,如同婚禮上的誓詞,未來如何,要一起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