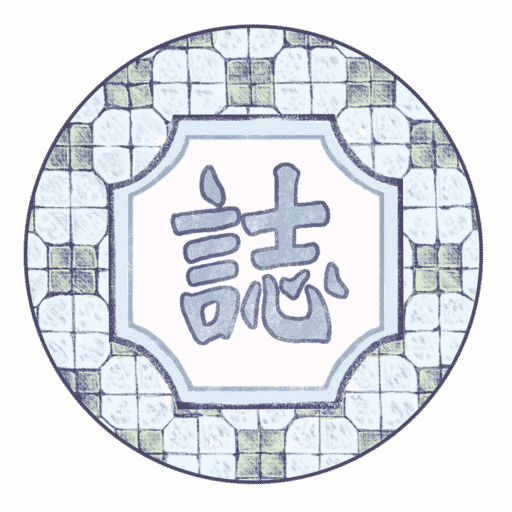訪問之前,記者在網上搜尋Sam Bickett的資料,往往會見到一個西裝骨骨的外國人身影。記者看到不同的報導都形容他為「美國銀行家」、「美籍律師」,有些更寫了他月入十多萬港元⋯⋯記者好快就將自己對expat(居港外藉人士)的刻板印象都放在他身上——離地、有錢⋯⋯。
「其實我支持Sanders(桑德斯)的理念⋯⋯」——與Sam閒談之間說起了去年美國大選的候選人,然後Sam說:「我覺得我們都是很關心人權的人吧。」
對了,這時記者才想起,作為一名美籍律師在港被判控襲警罪成立,要入獄四個月,刑期不算太長,Sam大可不上訴,直接認罪,完成刑期就回國,但Sam堅決要上訴,「由小到大,身邊的人都知我是一個十分固執的人⋯⋯我沒有做錯什麼⋯⋯我會繼續為我自己的勸利奮鬥、為這個城市的法治奮鬥⋯⋯」。
雖然Sam表明他對香港的法制已失去信心,但是上訴此舉又好像代表他對法律還未完全放棄,「我仍然希望法庭還是獨立運作」。事實上,Sam在成為律師以前,已知法律並非一個童話,但他心中對法律往往又留有一些希望⋯⋯。在Sam身上,記者找到現實與希望之間的拉扯,到底是什麼令Sam有這個矛盾?又是什麼令他繼續走下去?
人權議題往往找上他
Sam在法律博士畢業後的那一年,就嚐到了法律的甜味。
Sam畢業後就在一個波士頓的LGBTQ+機構,「Gay & Lesbian Advocates & Defenders (GLAD) 」工作。Sam形容,「那是我第一年做律師,也是我最為自己驕傲的時刻」。Sam憶述那一年,「那年我們嘗試去挑戰一條不容許同性伴侶結婚的法律,那一宗案件最後告到去美國最高法院,最終令同性伴侶可在美國結婚」。
不過,Sam在此之後成為了公司律師,原因也很現實,「在美國讀法律是十分昂貴的,所以在我幫人之前,我要做公司律師,因此最後我就在一些企業裏工作多年」。其實Sam成為公司律師後也繼續幫GLAD工作,「當時我們的州份想通過一條有關反對欺凌的法案,GLAD也有參與其中,因為LGBT的人被欺凌的比例比其他人多。我就是負責這個project」。

Sam承認,在企業工作的每個人都總會有質疑自己價值觀的一刻,但Sam就表示,他主要做反貪的工作,他仍然為自己的工作感驕傲。幾年以後,Sam因為一間英國藥廠在中國被指賄賂醫生的案件來港,最後亦因為喜歡香港的人便留下來了。「在波士頓,人人的學歷都太高,人人都喜歡談論政治、公共政策和批評政府⋯⋯我以為世上每一個人都是一樣,於是我初來到香港時,就跟人講政治,那時人們會望著我,以為我是瘋了似的!」
那是Sam初來報到的2013年。
翌年遇到2014雨傘運動,Sam便目睹身邊的香港朋友越來越關注公共事務,也見到年輕人越來越關心身邊的人,再不似以前只關注金錢和只顧自己。Sam覺得去到2019年,他見證了港人的覺醒。
2019年發生的事間接地令Sam因襲警罪入獄,但這亦令他與社會邊緣人士再次連結起來。「在香港,制度是幫不到一些人的,尤其是我在獄中遇到的人,好像一些曾經做過黑社會和毒販的人。沒有人想自己的孩子想成為毒販的,是制度令他們沒有選擇。」Sam說。
在獄中,Sam覺得自己得到的待遇是不錯的,Sam指這是因為他是一個外國人,加上律師、領事也會常常找他會面,因此懲教人員會確保他不會不高興,又會把一些不恰當的畫面收起不讓他見到。
「懲教人員是不理政治的,他們不會理藍絲或黃絲,越少問題發生對他們來說就越好。」Sam說。
可是,有些人就不如Sam幸運,「我有個來自中非的朋友在獄中投訴,要求增設多點風扇,但他就因此被單獨囚禁,為什麼?那是因為他敢去投訴」。Sam道出殘酷的現實,「有時(懲教人員)會對囚犯好,但如果你敢去為自己爭取一些權利而你又不是privileged(有地位)又不認識與傳媒或領事,那他們(懲教人員)會令你生活很難過」。
作為在獄中較privileged (特權)的人,Sam並沒有視沒有特權的人為他者,他更想為他們做些事,「我現在有一些最好的朋友是囚犯來的,他們有些以前是毒販。我希望在我的案件結束後,我可在這個範疇做些事。我想做有關人權的工作,為被社會排擠的人發聲」。在2021年香港獄中的所見所聞彷彿把Sam帶回波士頓畢業的那一年—人權的議題又再次找上了他。
童年貧富之間:法律可助人 也可以變得腐敗
可是,法律是把雙刅劍。
Sam自幼父母離異,父親是一個衣食無憂的中產,可是母親就是一個窮困的殘疾人士,一直都需要政府援助。Sam自小就在這兩個家生活。
「這令我感受到法律是對有錢和有權力的人有利的,而像我母親這種人,感覺上法律好像就是設計出來去排擠他們一樣」。
Sam解釋,在美國,有錢人可以負擔起游說立法者的金錢,從而保障自己的利益,同時,有權有勢的人更容易接近立法者,立法者有時又是有權有勢的人,所以有時法律就是由這些人制定。
但為何Sam仍選擇讀法律?Sam解釋,「我感覺法律是一個武器,它可讓我們爭取自己的權利,甚至可為他人爭取權利。可是,正正是因為法律十分強大,所以它有時也會被人濫用⋯⋯我想知道法律是怎樣運作的」。
Sam亦坦言,法律被濫用的情況常常出現,「不幸地,我們常常見到的,是有權有勢的人令法律腐敗,法律好似是被有錢人用來保護自己的財產」。Sam舉例,「在社會運動之中,通常令那些反對運動的人憤怒的是破壞財產的行為,而非針對個人的暴力、警方的暴力、窮人的痛苦⋯⋯」。但Sam沒有放棄法律,「我們需要更注意法律會變得腐敗的可能性,然後嘗試令法律不這樣(腐敗)。」
Sam強調,他到現在仍然是相信法律可以保障人權和彰顯公義。
兩地法律體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Sam認為法律不只在自己的成長地,而是在世界每一個地方都是可以被有錢人和有權勢的人濫用。
Sam指無論是香港或美國,也有不少警員犯了法卻不用承受後果的情況。但Sam強調,在美國如果警員犯法的畫面被拍攝了下來,通常這些警員都會受到懲罰,雖然也有例外,但他相信情況正在改善。對於法庭,Sam則認為美國法庭的運作還算可以,若有裁判官作出了一些不當的行為,人們可以投訴,要求裁判官被調查。
不過,Sam就表示他不認為在香港裁判官或警員會因投訴被調查,「至少在美國你會有個機會(投訴),在這裏好似沒有機會。你可以做什麼?向監警會投訴?笑話。向法庭設訴?他們會保護裁判官」。Sam認為,裁判官做了不恰當的事時就要先停職受查。

Sam舉例,「如果一個裁判官在庭上抨擊示威者;如果一個裁判官單單因為一個刺了別人一刀的人是『黃』就判他入獄9年,但又忽略了有『藍絲』也是刺人卻只被判囚3個月。這些裁判官都該被停職」。
Sam又補充,「當然,法官和裁判官的工作不能被干擾,但他們的判決是在法律之外的話,他們就該被查」。
但是Sam仍然抱有希望,「我不相信這裏的法庭是完全腐敗的,我相信我們見到的是法庭用了一些不好的法律,但大部分法庭仍然是跟從法律,雖然這些是不好的法律」。
或許就是一直以來內心的一點光,才令這個見盡風雨的律師一直不放棄法律;又或許是要有這種人,制度才能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