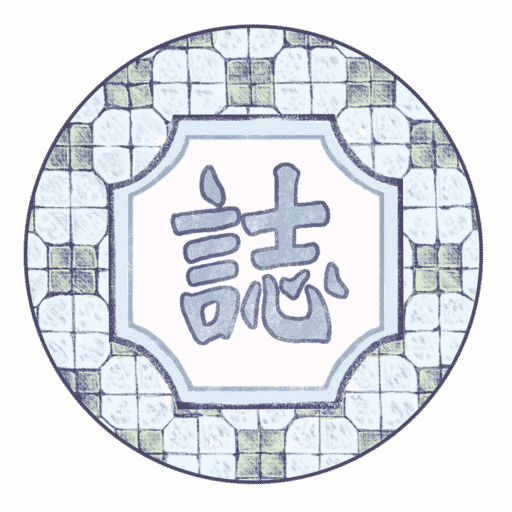序言—
2022年7月11日,35名電影人聯署《香港自由電影宣言》,表示堅持「忠實拍電影」,對抗電檢處在國安法護航下一再禁止電影上映。今次香港電影人的聯署不再如上世紀90年代反對黑社會入侵,而是宣示香港自由自主意志,因為「電影到底是自由的藝術。沒有自由的電影終究會枯死。」
《香港自由電影宣言》節錄—
「所謂『電影』,就是創作者面對世界的姿態。不論它是放在傳統戲院還是串流平台,是在大銀幕放映還是在手機上播放,只要作品能呈現出創作者站在現實面前的某種取態或想像,它就應當被稱為『電影』。
要在當下的香港拍電影,須面對的困難與風險之高,當算是香港歷史上前所未見。但弔詭地,現在必定是最適合拍電影、我們最需要電影的時機。我們寄願自己100%的從電影裏來,往電影裏去。我們相信,電影與倫理、政治、人生,窮根究底最後都會走到同一個終點;把電影做好,就是把自身的種種方面都做好。」
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
電影帶我們遊走於各個時代,創作者忠於自己,透過影像訴說大時代的喜怒哀樂。創作者在「壞時代」中,能夠將「壞時代」拍成電影,均取決於電影人屢敗屢試的堅持。驟時間,螢幕閃出「勿忘初衷」亦觸及紅線,不刪減便不能上映,審查步步進逼,誰主導這條紅線?紅線不斷劃圈為界,創作人如何從囚牢破繭而出,實踐在這兒說那事的創作自由?
電影審查於歷史上並不是新鮮事,除了有關暴力及色情等道德審查,政治審查幾乎能主導一部電影的下場。今日自由奔放的台灣,曾經歷超過半個世紀「黎明前的黑暗」。追溯至1930年,國民黨戰時文化委員會訂立電檢制度,凡不符合國民黨信念與教條者,通通禁絕。
在台灣「新浪潮」電影出現前,台灣戒嚴近40年,國民黨政府數度修正《電影檢查法》。當時電影創作處處受限,開拍前事先提交劇本予新聞局審查,情況如今日的內地市場。既要求劇情要遷就政權的道德尺度、立場,只要政府認定題材敏感,均會被禁。懸在創作者頭上的戒嚴令,讓電影人連連受挫。
誰沒有比誰高尚,上世紀七十年代英殖民地政府一樣對電影進行嚴謹審查。早於1909年,政府開始電影審查;二戰後,作為英帝國港口城市的香港,成為了冷戰時期的政治角力場,港英政府數次修訂《電影檢查條例》,以「政治中立」為由審查反共與親共電影,與台灣相似,送檢的電影出現某國國旗,也是審視的重要項目。
台灣電影經歷過「最壞的時代」,香港電影經歷過商業上的黃金時代,但今日的台灣以擁有無窮創作自由為傲。港區國安法的大環境之下,香港政府於2021年6月修訂電檢指引,增添了有關考慮「國家安全」的章節,香港電影曾經擁有的自由是否不復再?
今年的「鮮浪潮國際短片節」,14套本地短片中,故事角色名為「燕琳」的《Time, and Time again》(下稱《Time》)不獲電檢處批出放映證而成為「禁片」。而講述校園高壓管治的《群鼠》則在放映前最後一天才獲批,並被評為三級。兩部作品遭受不同的對待,內部「紅線」依然隱晦不明。
創作者與觀眾在壞年代不拘泥作品的長短及播放方式:我們對「電影」的界定不再是90分鐘的電影,對「香港電影」的界定也不侷限於在香港戲院放映,或必定要走過金像奬紅地毯的作品。香港短片蘊含我城的千言萬語,縱有作品被禁,亦有含苞待放的作品被迫「放逐」到海外,留待我們在「牆外」探討、欣賞。只要我們着緊我們的說話,我們一定找到看電影的機會。
《誌》在<禁片年代>訪問4位今屆鮮浪潮的創作者,了解作品的底蘊,藉此讓他們親自解說,仍然在香港拍電影的因由。
採訪 / 黎祉妤
編輯 / 關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