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很多人眼中曾經風光旖旎,如今這都市彷彿被黑雲壓頂,恐懼就存活於每個人心目中,如影隨形。免於恐懼的自由,成了一幀海市蜃樓。
麥海珊拍了一齣紀錄片《誠惶(不)誠恐,親愛的》,探索恐懼、自由與希望的本質。一如既往,她用了相當詩意的錄像方式,追訪及紀錄了2019年至2020年三位家長的心路歷程;用特寫鏡頭,凝住情緒的流動:不論是藝術家兼區議員張嘉莉的坦率;政治漫畫家黃照達的感觸;作家及理大教師張婉雯的內疚,也也呈現於銀幕上。恰巧,選的三位也是藝術家,更重要的是,他們是和我們經歷過2019年的香港人。
恐懼是種好意,不是壞事
《誠惶(不)誠恐,親愛的》去年10月在釜山國際電影節作世界首映,11月於香港亞洲電影節放映。但是疫情反覆,最終延至近兩個月才在戲院上畫。電影看似描繪人在社會運動、疫情間油然而生的恐懼,但其實拍攝起點始於2018年:「當時未有反送中運動,我想探索一下雨傘運動後幾年,香港人的不穩定性:到底還要不要生小朋友?那種憂慮和恐懼,讓我覺得幾得意。」
其後她篤定實行,便向藝發局申請資金,在烽烽火火的社會運動獲批。兩年爾爾,回首已是百年身,「電影於2019年至2010年期間拍攝,三位受訪者說了很多擔憂,對小孩成長或香港將來的憂慮,最恐懼的是,現在通通都發生了。」
麥海珊選定恐懼為命題,源自切身經歷。九十年代末,她患上了驚恐症,當時並沒有太多人關注精神健康,第一次發病,是非常偶然的情況。一天,她救了在一隻瑟縮於家中窗外的小貓,因小貓的尾巴受傷,便為牠塗上藥膏,突然,她覺呼吸困難、心跳加速、氣促和作嘔,甚至想暈倒下來,便立即召了救護車送院。自此,不論走在熙來攘往的街道,或是留在幽暗的寐室,時而出現這堆徵狀,原因不得而知。

藝術家角色,要紀錄和分享故事
電影上映期間,香港的文藝界不停受到左報的猛烈抨擊。《誠惶(不)誠恐,親愛的》是去年9月、10月通過電檢,麥海珊看得較輕巧,不覺得這時候能夠於戲院播放這部電影有何特別意義,自覺它好普通,都是在做往日在做的事。
現實上,創作當然沒法完全自由。但是對於香港日漸收緊的創作自由,她提到國安法是很大的因素,「這是很明顯的限制,我們不是甚麼都能說,which is以前可以嘛。」她直言,自己不算是很恐懼,也可以說是「無得好驚」,因為不知道紅線會不會郁:「總之,這一刻不犯法,而我又覺得想去做、對香港有益處的創作,我就繼續去做。」
三位受訪者是藝術家,影片中又特意展現不少藝術創作,問到麥海珊如何看藝術家在紛亂世代中扮演的角色,她頓了頓:「好少思考這些問題,唔識答添。」她沉思良久,緩緩吐出幾口氣,細膩理清一字一句:「我覺得,第一是要紀錄。現在我紀錄了2019年三個父母在那一個社會氣氛下,說了這些話,有這些感覺和情感,這也是 documentary-based work 本身的功能和性質。」
她再怔了一下,才續道:「第二是分享故事,這電影做的是情緒層面的事,很多人看完很感動,甚至哭了。我認為電影就是共通點,讓我們互相聯繫起來。我們現時沒法再說,我是我,你是你,因為大家都是一個連結,香港的抗爭狀態,都是不同點的連結。」如果故事能夠觸動人,引起共鳴,甚至分擔到人的情緒,都可以是亂世中藝術家的其中一個崗位。
恐懼與希望,其實像對雙生兒。
影片中,麥海珊不停詰問受訪者兩者關係,然而換成今次問她,答案卻是如此不亢不卑:「現在真的沒希望嘛,例如你不會希望明天香港突然有民主,不是你主觀希望就會發生。但沒有了『希望』,又不等於不可以自主。不知這些算不算希望,盡量在自己崗位上,思考還有甚麼可以做。」要自主免於恐懼中,就是不要失掉對未來的希望。
電影開首是夜幕低垂的茫茫大海,浮沉迭變,結尾卻是香港日常城市景觀——被鐵絲網環繞的行人天橋樓梯,一人上斜跑奔向遠方,讓人意會到,只要人還在,香港就在。

《誠惶(不)誠恐親愛的》
30/4 (五) 21:50

其後,麥海珊去了看臨床心理學家,又學禪修,花了三年將病治好,也對如何與恐懼共處有一番領會:「恐懼不一定是差,恐懼甚至可能是種好意。例如電影中,張嘉莉會說恐懼令人好驚,但會幫你推進。佢話,傘運之後自己唔知點,做那個將一千隻雞蛋擲到身上的行為藝術,因為覺得幫唔到下一代。但是反送中運動,反而讓她更積極,例如參選區議會,正是『好嬲、好驚』所推進。」
在她眼中,恐懼是情緒,會來會走,來去如風,會提醒你前面的危險。
「但它有時提醒得太大力,令我們疼痛,令我們錯亂,令我們誤判現實的狀況。我們要做的是,我們要辨別到,哪些是情緒,哪些是真實,並學到讓恐懼與你共存,甚至讓它幫助你。不要被恐懼控制,令你不能自主。」
回到電影上,恐懼讓三位受訪者看清心中的渴望,思考自己願意付出的代價。一種情緒有趣在,它可以是很個人、很私密的層面,也可以是很政治、很公共的層面,明明讓人敬而遠之的東西,卻原來換個角度,可以有正面積極的作用。
為母則懼,長憂九十九
然而,當你為人父母,所背負的思慮,又是截然不同。
《誠惶(不)誠恐,親愛的》另一個主題,在於爸爸媽媽的身份。影片中不斷訪問他們,恐懼和自由的關係、恐懼與希望的連繫,引發很多思考。三位父母,性格迴異,切入點均有不同,但麥海珊拿捏得宜,尤其觸動人心。
影片中,張嘉莉不想離港,畫了一幅畫,思考走到未來,問一問長大的女兒,會不會怪責她沒有帶她們離開香港,當中的惴惴不安,感慨良多。黃照達看似理性,說起獅子座介意別人眼光,做創作都做他人所想,但生兒育女後全情投入,反思人生,孩子行為其實都映照出成人本來的模樣⋯⋯。
張婉雯更是率真感性,面對為香港付出的年輕人會內疚,但轉念又想到家中年幼的兒子,為母既讓人欣喜,但限制讓人無力、愧疚,同時長憂九十九,「如果我個仔今年17歲想上前線,咁我會點?我會立刻學武功,同佢一齊上。」2019年後的香港,誰不恐懼?但在恐懼間閃爍的人性光輝,永遠最亮眼。

藝術家角色,要紀錄和分享故事
電影上映期間,香港的文藝界不停受到左報的猛烈抨擊。《誠惶(不)誠恐,親愛的》是去年9月、10月通過電檢,麥海珊看得較輕巧,不覺得這時候能夠於戲院播放這部電影有何特別意義,自覺它好普通,都是在做往日在做的事。
現實上,創作當然沒法完全自由。但是對於香港日漸收緊的創作自由,她提到國安法是很大的因素,「這是很明顯的限制,我們不是甚麼都能說,which is以前可以嘛。」她直言,自己不算是很恐懼,也可以說是「無得好驚」,因為不知道紅線會不會郁:「總之,這一刻不犯法,而我又覺得想去做、對香港有益處的創作,我就繼續去做。」
三位受訪者是藝術家,影片中又特意展現不少藝術創作,問到麥海珊如何看藝術家在紛亂世代中扮演的角色,她頓了頓:「好少思考這些問題,唔識答添。」她沉思良久,緩緩吐出幾口氣,細膩理清一字一句:「我覺得,第一是要紀錄。現在我紀錄了2019年三個父母在那一個社會氣氛下,說了這些話,有這些感覺和情感,這也是 documentary-based work 本身的功能和性質。」
她再怔了一下,才續道:「第二是分享故事,這電影做的是情緒層面的事,很多人看完很感動,甚至哭了。我認為電影就是共通點,讓我們互相聯繫起來。我們現時沒法再說,我是我,你是你,因為大家都是一個連結,香港的抗爭狀態,都是不同點的連結。」如果故事能夠觸動人,引起共鳴,甚至分擔到人的情緒,都可以是亂世中藝術家的其中一個崗位。
恐懼與希望,其實像對雙生兒。
影片中,麥海珊不停詰問受訪者兩者關係,然而換成今次問她,答案卻是如此不亢不卑:「現在真的沒希望嘛,例如你不會希望明天香港突然有民主,不是你主觀希望就會發生。但沒有了『希望』,又不等於不可以自主。不知這些算不算希望,盡量在自己崗位上,思考還有甚麼可以做。」要自主免於恐懼中,就是不要失掉對未來的希望。
電影開首是夜幕低垂的茫茫大海,浮沉迭變,結尾卻是香港日常城市景觀——被鐵絲網環繞的行人天橋樓梯,一人上斜跑奔向遠方,讓人意會到,只要人還在,香港就在。

《誠惶(不)誠恐親愛的》
30/4 (五) 2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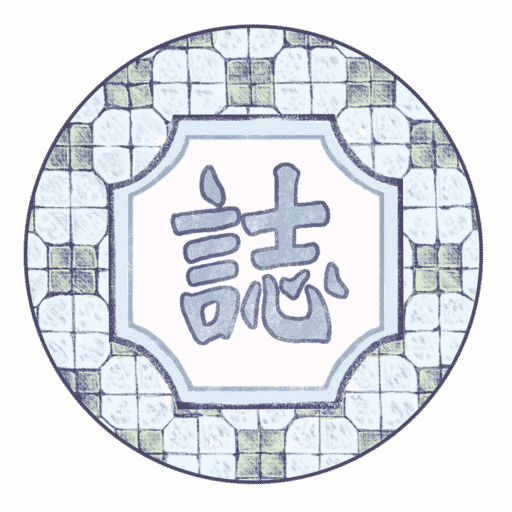
誠恐」:與恐懼共存,做自主的人.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