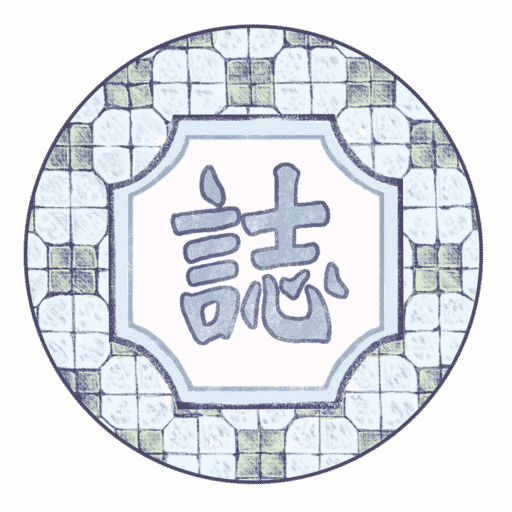「我覺得坐監都不錯,裡面有一大班朋友,又可以給自己靜一靜,可以讀讀書,跟朋友聊聊天,又不是太差。是不是很瘋癲?但其實我好正常,只是這個世界太瘋癲。」二十四歲的「開站師」袁德智說,他已規劃了十年來坐監。
「開站師」袁德智
用「瘋癲」來形容他或許貼切:在港區《國安法》的時代,多個政治組織紛紛解散之際,袁德智召集一班朋友成立「開站師」,在街頭講政治;在厭倦字海的時代,他不管有沒有人理會,仍寫下一篇篇千字文政治論述;有建制派團體到警總和他的母校中大示威,聲討「開站師」,他也一笑置之。
為了什麼?理由很簡單,只有「重聚」兩隻字。「如果沒有行動,我常常會覺得,有些人我永遠都不能再見。」

擺街站,讓群眾看見彼此
3月15日,袁德智在社交平台Instagram發了一個即時動態,召集自己的朋友,為民主派初選案(47人案)的還柙者擺街站,呼籲市民停下來為他們寫信。他們擺了一個下午,揚聲器用到沒電,就大聲的喊,那天共收集了約一百封信。
「如果留下來什麼都不做,那跟移民有什麼分別?」隔幾天他在Instagram寫道。
一切是由《港區國安法》落實後,好友張崑陽流亡那刻開始。那時起,他便要習慣身邊少了一位戰友,到後來「47人案」,梁晃維、鄒家成、岑敖暉等好友一個又一個被送進監房,其中張可森太太才剛懷有身孕,袁德智便覺得要為他們做些事,「如果沒有行動,我常常會想,有些人我永遠都不能再見。」
想幫助還柙朋友,最基本是寫信。擺了三至四次收信站,他想再行前一步,而非做文宣版「石牆花」,於是跟朋友一起創辦「開站師」,在街頭講政治論述和派單張。袁德智認為,街站的意義是empower(充權)整個公民社會,將絕望的人拉出谷底,以及讓眾人連結(bonding)。
有媒體形容,「47人案」是港版的美麗島大審。袁德智讀台灣學者吳乃德所寫的《臺灣最好的時刻》,裡面提到台灣白色恐怖時代,人們透過選舉在公民社會動員,領袖被看見了,人民才走出絕望。袁德智覺得,如今香港既不能搞遊行集會,選舉又已變質,那就要擺街站,讓群眾看見彼此。
他憶及一次街站,有一位太太為47人逐一寫信;亦有不少市民送飲品,為他們打氣。這些互相充權的行動,讓他重拾力量。「開站師的目標從來都是群眾,從來要面對的人都是公民社會,即是香港人,整個共同體,而不是政權。」
行動也連結起「開站師」成員。一開頭擺收信站,只得三個朋友答應參與,剛好不違反限聚令。後來行動打動到朋友們加入,慢慢擴展至今十多位成員,數十名義工,連自己也收了一張599G告票。
讀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的他說,Ontological(存在論)是他學過最重要的理論:不是做些事去達到某些目標才有價值,而是做那件事的剎那,價值已經存在。他認為擺多少次街站都不能直接換取民主,但它本身的價值,是在鼓勵別人、帶來希望。

豁出去
袁德智談政治論述時很有自信,像開機械槍一樣停不了,而且語速極快,雙手像指揮家般舞動。朋友們就稱他非常「長氣」,例如今年7月1日,他特別在《立場新聞》寫下5,998字評論,叫人不要放棄,比起六四前夕寫的3千多字文章還要長。
2016年他是中大學生會本土派內閣「星火」的外務秘書,早已習慣面對記者,說慣長篇大論。
不過,3月時記者曾邀請袁德智做訪問,結果他推給好友、前中大學生會副會長羅子維。2016年的經驗,使他害怕鎂光燈,不想被質疑搏上位,不想家人擔心,亦怕政治立場限制自己未來的路。
自4月決定做「開站師」,他便豁了出去,因為他想示範「以行動戰勝恐懼」。他形容人生已跟香港重疊,沒有民主自由,就不能規劃未來。
他的夢想是做日本時裝品牌代購,還想開一間酒吧,跟朋友喝酒聊天,但通通都要放下,「朋友遭受的苦難,令我記住一件事,我要將香港的未來放先於我個人的人生。」
有一次袁德智媽媽看見他的訪問,害她十分擔心,便對兒子說:「你知道現在有《國安法》嗎?」他只說自己能處理,然後返回房間。他跟兩位妹妹和朋友說好,如果自己坐監,便替他照顧家人。「我不想人生有憾,如果有家庭顧慮,那只能想辦法解決。」
他預留十年時間來坐監,就算這兩年入獄,出來只是三十多歲。「我覺得坐監都不錯,裡面有一大班朋友,又可以給自己靜一靜,可以讀讀書。能跟朋友聊天,又不是太差。是不是很瘋癲?但其實我好正常,只是這個世界太瘋癲。」
時局使人成長
袁德智中學經歷雨傘運動,一心想入大學參選學生會。後來他成功入讀中大經濟系,卻不想在動盪裡對著一堆數字,於是決心轉至政治與行政學系。第一年轉科失敗,第二年才成功。那是2017年,剛好遇上社運低潮,他每天在宿舍打機拍拖逃避現實,而轉系成功成為他人生的點燃劑,將他帶進政治空間裡。
從堅持轉系,到今天繼續發聲,記者問他如何堅持,他便打斷否認,說堅持兩字從來與他無關:「我幼稚園學彈琴,中途就放棄了,接觸新事物都是三分鐘熱度。就算在小事上,我也沒有責任感,時常遲到。這樣的人怎說堅持?」
中大學生會前會長、袁德智的莊友周竪峰形容,袁以往很flamboyant(浮誇),喜歡表現自我,想法天馬行空,但說的比做的多,更有一股蠻勁去做事,而近來明顯變得內儉沉實。「過了這麼多年,人始終會成長,不太現實或者比較幼嫩那部份開始成熟了,但當初那份衝勁,好想做些事的精神就依然留下來。」周竪峰說,知道袁德智成立「開站師」時十分擔心,但覺得袁明白有何風險,作為朋友雖痛心但仍會支持。
袁德智自嘲是後排冷氣軍師,但前排的人相繼離隊,結果他就站了第一排。這是時勢使然,逼他急速成長,他擔心連自己都走了,便沒有人會為香港做些事。「以前有人叫我寫文章,我會過幾天再寫,因為知道其他人最後會幫我,但現在發現沒有人再幫我了。」

習慣孤獨 只為了重聚
在凌晨,不時會看見袁德智活躍於社交平台,有時他會在Instagram分享歌曲,多半是抒情歌;有時他會翻貼舊照,如7月9日的午夜,貼了自己與朋友在台灣時的照片,相中有浸大前學生會會長方仲賢、流亡中的張崑陽,和正在還柙的梁晃維。
他自大學投入政治,逾半朋友來自社運圈,慢慢他們走的走,坐監的坐監。一到深夜孤獨就浮現,教他渾身無力,只能躲在房間裡,蓋著被子看手機、聽歌和看舊照片。他說像在聽朋友們跟他說話,和大家再次相見。「好撚辛苦,好撚想死,如果大家還在就好……。」
袁德智多次提及,他曾拜訪已故台灣革命家史明,當時史明對他說過一句話:「要習慣孤獨」。
袁德智把話聽進心裡,但仍在嘗試習慣。「Sunny(張崑陽)流亡,都不太習慣。去到更多朋友入獄,學生會的朋友都離開了,有時候很傷心,點解咁撚癲(為何那麼瘋狂)?我以往認識的人,都是為了香港,完全沒有私心,不是想做政棍,只想有民主而已。」
他相信行動能戰勝負面情緒,當有事可做便沒空閒想孤獨,「用行動跟情緒共存」。
台灣民主路同樣艱苦,1949年國民黨在台灣實施長達三十八年戒嚴令,期間多人為爭取民主自由而死傷、囚禁與流亡。1952年,三十餘歲的史明刺殺蔣介石事敗,坐香蕉船亡命日本,一走便是四十一年。他隻身避走異鄉,白天賣餃子,夜晚寫台灣史,又到海外演說。每天節衣縮食,只求有天回到台灣。史明嚐到了苦,慢慢習慣孤獨,他在回憶錄裡寫道:「但是在最困苦時,我都告訴自己,『這是為了革命在吃苦』」。
孤獨四十一年,談何容易?袁德智坦言自己未必有史明的能耐,但不會為自己的抗爭路設限期,因民主是他和香港人的共同心結。「心結就是,可以暫時放下,但不會有完結的一日。就算想放棄,有事發生還是會站出來。」
一夜凌晨,他分享了台灣樂隊「溫室雜草」的歌曲《在這個年代,找不到浪漫》,歌詞是這樣寫:「在這個年代,找不到浪漫,子彈和逃難,都與我無關。在這個年代,我們不浪漫,我們的浪漫,都只是糜爛。因為妳快樂所以我快樂。」
步入「後反送中時代」,牆外有人灰心失意,有人移民逃難,袁德智選擇留下來堅持,以香港為志業。
這一切為了什麼?
滔滔不絕的他首次停下來,用了十秒去想這條問題。「我爭取民主是為了我的將來,也是為了每一個人的將來,每一個重視香港的人的將來。如果你不解決這個問題,其實你所有規劃都是虛無。為了我們每一個人的未來。」一切是為了一個讓大家「重聚」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