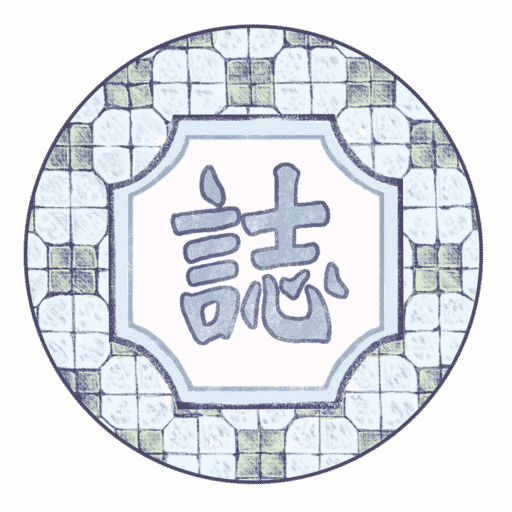若流砂在河口聚成洲,電影《白日青春》就是導演劉國瑞反芻33年人生的成果。
2008年,18歲的劉國瑞從馬來西亞來港升學。除去90後、馬華、新移民等的身分標籤,年輕人投身馬來西亞與香港的變革浪濤裏,生命能迸發出怎樣的可能性?
劉國瑞並不是在拍2023年版的《投奔怒海》。這位馬國少年沒有從旁觀者的角度看香港,在他創作的「公路電影」中,他「下車」走上公路,置身其中,感受大時代。剖開《白日青春》的肌理裏頭不僅是難民,電影母題是流動的年輕人們,也是他們在各地社運浪潮下詰問的身分與未來。

漂泊的根源:那群離家的馬華一代
《白日青春》講述昔日從內地泅水偷渡來港的的士司機陳白日,與巴基斯坦難民二代的哈山(莫青春),這兩代難民在香港相遇而引發一場逃亡之旅。對劉國瑞而言,書寫難民的故事是一件很貼身的事。「我覺得那種狀態跟我很接近——你對於未來的那種不確定性 ,譬如說你來到這裏,但你不知道未來又會在哪裏?我想很多馬來西亞華人都會有這種心理狀態。」他說,電影的重點在於那種流落異鄉而失去的家庭關係與情感上的缺失。

劉國瑞是第四代馬來西亞華人,自小在馬國西邊臨海小鎮麻坡長大。麻坡一字源自馬來語「Muara」,意指「河口」。據說是商旅途經寬濶的麻河河口而命名 。河口自19世紀中葉起匯聚南來的福建、潮州經商人士,劉國瑞的祖先從福建流徙到馬來西亞,祖父和爸爸也在馬國出生。
他說:「其實那裏就是我們的根,我們的家。但問題是,你在這些社會主流並沒有甚麼話語權。」
馬來西亞是一個多民族國家,馬來人/土著佔最多,其次為華人與印度人。2022年底,馬來西亞華人約有690萬,佔總人口兩成。馬來人與馬華追求的馬來西亞是截然不同的。
「在這樣一個多元社會,由於馬來西亞主流都是伊斯蘭教徒,超過60%。所以對於很多華人來說,當你想發展一些東西的時候,其實你會感覺到被限制,但不是所有人(有此感受),我想也不是絕大部分,可能只是少數。」劉國瑞說。
無以名狀的故國
每當談起馬來西亞,劉國瑞總會加上很多前因後序去描繪自己的想法。因為他理解自己從來不是馬來西亞主流,尤其他長大的小鎮是一個純粹的華人圈子,自少在華文學校唸書,他說就像美國唐人街的華人不會說英文的感覺,「所以有時候別人問起馬來西亞,也很難清楚地表達」。不知從何說起的家鄉甚至讓他一度抗拒寫字,儘管他從小便最愛翻閱文學作品。「因為我經常覺得文字是很有限的,後來我喜歡拍電影,因為我覺得它的表達接近現實,但又有一種介乎虛與實兩者之間的感覺,但後來又覺得不是這樣。」他謹慎地說。
馬華年輕人雖然在馬國土生土長,但受制於馬來西亞產業結構,與馬來人優先的經濟政策,如升學也受配額限制。「馬來西亞有600、700萬華人,當中可能有幾十萬到100萬去了別的國家。其實這是一種生命尋找出路的概念。」

當祖先流徙到馬來西亞扎根,後代漂往外地發展,投身金融的華人後裔大多會到毗鄰的新加坡,發展華語創作的會漂往台灣。「你對這個社會有感情,你沒法控制⋯⋯沒有話語權,那種東西,其實是很傷心的。」《白日青春》以清代詩人袁牧的《苔》為題:「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寄寓生命自會尋求出路。那是陳白日,也是哈山,但某程度更像劉國瑞自身的投射。
哥哥和姐姐先後赴台灣升學,18歲的劉國瑞亦順理成章海外升學,最初他漂流的目的地不是香港。他曾打算到日本,礙於留學費用高昂,父親亦揮不去二戰的陰霾,在麻坡老一輩人的記憶裏,是頭上那數十架轟炸麻坡四天的日本戰機。剛好老師建議他投考香港的大學獎學金。18歲的他渴望經濟獨立,遂拿著香港城市大學全額獎學金來港。他笑言,「其實沒有理想的,純粹為錢,因為三年(當時大學制是三年)很快過」。
90後馬國少年 遇上兩地變天
2008年,劉國瑞來到香港修讀市場學。香港主流商科同學目標明確,與他隨遇而安的性格大相徑庭。他自言不是個目標明確的人,「對我來說, 其實是玩的,我又不覺得有些事情一定要做」。畢業後,劉國瑞到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任助教,同時也在摸索自己的路。那時,他在山城旁聽中大政治與行政學者周保松的課堂,閒時泡在電影裏頭,亦漸漸走進紀錄片的世界。而迎面撲向劉國瑞的,是馬來西亞與香港交錯的社會運動浪潮。同一個時間,不同的地域,亞洲各地各自踏進躁動的年代。
劉國瑞2012年開始學習拍攝紀錄片,遇上反國教浪潮。他說,當時紀錄片仍是很小眾,「某程度上和社會服務差不多,即是拍攝身邊的人、關注弱勢群體,那時的概念是這樣」。除了到社會運動現場拍攝外,他的鏡頭還觸及無家者、傷殘人士和難民二代。
有時劉國瑞當攝影師,沿導演的邏輯去閱讀香港;有時他帶著自己的意識去發問,透過鏡頭去理解同樣漂泊的異鄉人。「對於在這個城市缺乏資源的異鄉人,我覺得可以幫就去幫。」他到支援外傭媽媽的團體「Path Finders 融幼社」當義工,偶爾他帶著器材拍攝這群體,但更多時間純粹照顧孩子,換來媽媽喘息的空間。

那段時間,他一年回國五、六遍,或回家投票,或參與公民社會的活動。馬來西亞於2007年出現首次「潔淨選舉聯盟」集會(馬來語稱Bersih,意指「乾淨」),推動選舉制度改革,揭開往後十年馬來西亞社會運動序幕,一度讓馬來西亞展開跨越族群對話的可能,以公民而非國族的身分去探討未來。在這十年的經歷,就像一場公路電影,他有時在車上,有時下車,下車最多還是香港,馬來西亞與香港就是一張Round-trip ticket(往返機票),拉開「隨意門」,便栽頭進去,「那時不覺得自己是脫離馬來西亞的,是兩邊同時參與。當然Physically(身理上)在香港的時間比較多,而親身參與最多的也是香港。 」
劉國瑞亦見證過香港主權移交以及最大的兩場社會運動。2014年香港爆發雨傘運動,縱然歷史脈絡各異,但兩地卻先後冒起催淚白煙。傘運結束後,香港社會彌漫著一片無力感,而他身邊的朋友開始渴望離開香港。「那時感覺很強烈,好像我在馬來西亞感受過的事情,在香港又感受多一次。」這份熟悉感驅使他拍下首齣劇情短片 《九號公路》,而故事主角正是由香港逃往台灣的港大畢業生。

身處各自變革的浪濤裏,兩地又會否有溝通的可能?2018年,劉國瑞與《亂世備忘》導演陳梓桓一同赴馬來西亞,展開一趟播映《亂世備忘》的公路旅行。他們自費租車自駕,穿梭吉隆坡、怡保、檳城、馬六甲和新山五個城市,辦了七場放映會。縱然放映會錯過當地的社會運動,但觀眾反應卻超乎劉國瑞預期,「那齣戲帶給觀眾一些反思:其實你追求的是甚麼社會?而我以為沒有那麼多迴響, 但後來確實出現了有些討論。」
忒修斯之船
這14年遊走兩地的經歷一直滋養他的創作。《白日青春》開場一幕,陳白日在鴨洲獨自祭祀亡妻,遙對大陸鹽田,以及那片與妻子訣別的大海。那次拍攝,他並非首次踏足鴨洲,他曾為陳梓桓《憂鬱之島》掌鏡,親睹渡海偷渡的倖存者,每年拜祭殁沒駭浪中的親友。後來,他為《白日青春》回到同一個鴨洲,然而這次關注點從「到底香港是甚麼」的詰問,轉化成另一個肌理的香港,探進不同年代漂泊到港的異鄉人的人性幽微處。

若漂泊是劉國瑞創作的母題,那在母國培養對政治身分與多元文化的敏感度,足以讓其作品擁有突破主流敍事的可能。他第二齣短片《末路窮途》聚焦巴基斯坦裔移民家庭,而《白日青春》也延續他對在港巴基斯坦裔社群的關注,但主角換成政治難民和他們的無國籍小孩。
「香港是一個開放的地方,其實我也可以拿到香港身份證。雖然我是華人,但不是華人為甚麼又不行呢?」 他思考着:撇除所有的政治制度、外在因素,在哲學上究竟如何定義你是甚麼身分的人呢?「其實這個是很忒修斯之船的,究竟香港人的定義是甚麼呢?」劉國瑞問。
劉國瑞討厭「少數族裔」的標籤,究竟甚麼是少數?有時卻苦無更準確的形容詞。電影裏哈山被賦予「莫青春」這個中文名,在中文課學習《苔》。「某程度上我就像老師,老師只不過是有一種寄語,想你做得更好,但是否一定要這樣呢?」
在劉國瑞眼中,香港昔日的開放性容讓人流徙到香港。「而這個脈絡、香港的歷史是無法複製。某程度是冷戰產物,和台灣一樣,但台灣有些不同,台灣只是國民黨的選擇而已⋯⋯但香港不是,它不是英國政府所選擇,因為英國最初是不想要香港的。」
回到歷史本身,香港是在特定時代背景下,長年由外來的人從上而下去建立制度,然而由人從下而上建立的公民社會,兩者近十年開始發生不能消弭的衝突。

見證時代的反撲 在場不在場非最重要
2019年6月,香港爆發反修例運動,港人對身分認同起了新的理解。當時劉國瑞剛好開始動筆創作《白日青春》,而他正帶著《末路窮途》到世界各地參展。兩個月後,他人在紐約,完成了《白日青春》的劇本,而香港亦變了樣。
「2019年之後會發現自己的價值觀和主流馬來西亞社會相差很遠。可能簡單來說,對於自由的理解有很大的出入,會令你懷疑究竟是否真的想和這班人一起生活?」反修例運動讓劉國瑞意識到自己的價值觀,變成馬來西亞主流社會少數中的少數。而他卻漸漸變成香港的主流。
疫情三年,他無法回國,彷彿脫離了馬來西亞脈搏。馬來西亞社會正經歷保守力量的反撲,而香港亦步入離散的年代。

劉國瑞2020年曾有一個赴美升學的機會,但他卻選擇留在香港。對於2020年的時空,他認為香港正處於一個歷史性時刻,要是香港發生大事,而他只能在美國隔岸觀火,一定會很難過。不論好事或壞事,他也希望與香港一同經歷。「有事發生的時候,我會希望我人在現場。即使坐地鐵我就可以去到現場,那時候是這樣想。」後來,他留了下來,把旅途上的種種提煉成《白日青春》。
拍竣這齣電影之後,他的想法稍有改變。在場與不在場不再是最重要的事,他自覺多了一份責任,「講得核突啲(說得肉麻點)」就是要把香港和世界連結起來。
如今劉國瑞對去留換了另一個看法。「我已經將我人生大部分,在香港的情感都放進這戲,難以短時間會再有下一齣。」他想積累能量去創作,而這件事或許需要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才能辦到。
若把生命推向極限,人會如何掌控命運?沒有話語權的哈山搶槍保命,又能否為生命掌舵?如今不同的觀眾對電影有各自的投射。
揚帆出海的小子,是哈山,也是劉國瑞,他說下一齣電影希望處理更個人的故事,一個關於馬來西亞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