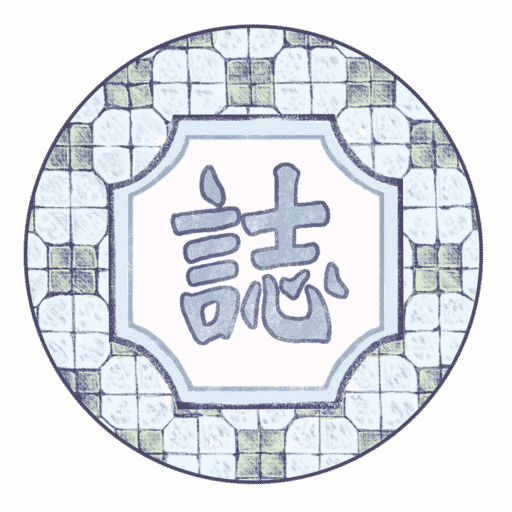無以名狀的「憂鬱之島」,一種流動的身份狀態,該從何說起?
經歷雨傘運動,陳梓桓完成前作《亂世備忘》之後,後雨傘年代瀰漫着低沉的政治氣氛,公民社會難紓鬱結。2017年陳梓桓正好承受着沉鬱無力的情緒,抱着「總要有人拍,有人記錄」的心態,著手創作《憂鬱之島》,計劃以半紀錄,引入戲劇重演的形式拍攝後雨傘的社會變遷。
拍攝期間,2019年發生反修例運動,香港遇上翻天覆地的改變,2020年實行《港區國安法》,香港人離散⋯⋯陳梓桓的創作原點回到香港人身份的思考。《憂鬱之島》重組的不再是一個島、一個人的歷史、一個時代,是牽引着幾代香港人不能自主的形態。
看畢《憂鬱之島》,腦海伴隨的,是零散的畫面。颯颯海風,輕舟搖曳,幾代人香港,是否注定漂泊?
今年7月《憂鬱之島》在東京率先上映,日本版海報以「在激盪年代的三個人物,以他們的視線重組香港身份」,其時珍寶海鮮舫沉沒的消息舉世震驚,日媒以此寓「消失的香港」,《憂鬱之島》的出現,對外國人而言就像海底尋謎。陳梓桓特別選出1973年從內地逃亡來港的陳克治、六七暴動不認罪的少年犯楊向杰、以及1989年天安門見證者人權律師林耀強,作為電影的主軸。陳梓桓坦言,《憂鬱之島》是一邊拍攝一邊創作,在演與被演的虛實之間,讓不同年代的香港人在影像相遇。不同年代的香港人在身份、理念上看似南轅北轍,卻有其感通。

「一開始覺得用憂鬱去總結2014年傘後(雨傘運動)的情緒,當我拍完(《憂鬱之島》)歷史的部份,我覺得憂鬱是貫穿每個年代。但凡曾思考香港人的身份,永遠因為這個思考付出很大代價。其實每個世代的身份認同不一樣,但同樣擁有一種情緒,因為香港是一個不能決定自己命運的地方。」
琢磨五年,鍊成《憂鬱之島》,陳梓桓可能是香港電影史上首位以「憂鬱」為香港命題的導演。
從幾代人的身上重現幾段沉痛的歷史,陳梓桓在創作的路程中拾檢考察香港歷史的砂石,愈發現香港人這個身份並不容易刻劃。「曾經有一位婆婆跟我說:『愈平靜的河是最深的』,我喜歡這句,喜歡這句⋯⋯。」言及此贈言,陳梓桓笑不合攏,他說這句話猶如暮鼓晨鐘,嚮導他在悠長深邃的長河尋找香港人的身份。
香港人的混雜性
2017年陳梓桓開始着手寫1967、1973、1989年的歷史劇本。直至2019年爆發反修例運動,他又再次走進示威現場,抓着城市的情緒拍攝,累積的影像愈多,創作上愈是迷茫。他沉思在2019年之後,這座城市和他需要一部怎麼樣的紀錄片。
「也曾想過,應否像《亂世備忘》那樣拍攝,在現場找真人,找故事,但其實唔work。唔work 的是運動的性質已不一樣,當Live Media已取代了《亂世備忘》要做的事,2019年需要紀錄片,但未必是這一種。」陳梓桓透露曾經打算將2019年的影像獨立成品,最後還是擱置,說到底,《憂鬱之島》探討的香港人身份,2019年是不能缺席。
陳梓桓在《憂鬱之島》的野心沒有停留在2019年一個面,或是一個點,在創作途中他有意無意地用幾代人的痛苦交織出今日的香港。由受訪者自述,跨代重演,情感上在投入與抽離之間,層層剝開香港人身份的面紗,直達的我們的心坎處—— 香港人的底蘊是甚麼?

夕陽西下,荒野稻草搖晃、船倉內沉靜的海浪聲、六四燭火與墳墓⋯⋯《憂鬱之島》畫面、聲音映照出幾代人的掙扎。陳梓桓坦言「貪心」地用幾個時代重新思考香港人的身份,它(香港人身份)就像海水一樣,永遠是流動的狀態。在大學讀政治出身的陳梓桓回望香港幾代人的身份,他發現在混雜之間,有很多東西有待發掘。
「無論是89年面對一個主權移交的香港;或者67年,極左的人想中共立即收回香港;或者73年一班人面對文革,失去自由但仍希望往自由的地方,他們都視香港為某種的定點。我好貪心地將多段歷史拼埋一齊,說出香港的複雜性。」陳梓桓說。
重演、自述、記憶
《憂鬱之島》更貪心的,是陳梓桓要求經歷2019年反修例運動的年輕人隔代重演舊時的香港人,甚至要受訪者重演自己的過去。時間是抹去歷史的催化劑,陳梓桓懷疑「人總是想說自己想說的話」,自述的呈現方式並不可靠,甚至對個人記憶包有懷疑,「三個人物接受過很多訪問,將自己的歷史說了百萬遍,反而不是我想要的東西。」陳梓桓放棄由上而下去敘述歷史,從追蹤拍攝、觀察受訪者、重演及兩代人對談,重新發掘、拼湊出一個時代。

陳梓桓跟拍了三個受訪者數載,有時興之所至,會安排一場戲給素人演員演回當年的情況,也給歷史人物用「演」或「被演」的方法重塑自己的記憶。
主角之一陳克治,在文革不願當農民,1973年冒生命危險攀山涉水偷渡香港,他擁抱香港的自由,八號風球下風雨不改在香港海岸暢泳。陳梓桓說進入電影後期製作,早已鐵定用陳伯在岸邊準備下水的畫面作為電影封面,「這很有代表性,這是他對自由的表現、堅持。」
陳梓桓安排兩位年輕演員在山頭重演文化大革命讀毛澤東語錄的一幕,陳克治夫婦也被安排當演員,事隔六十年,陳氏夫婦演回自己。劇中眾人振臂高呼:「毛澤東萬歲!」,與領導一唱一和。陳梓桓大喊「Cut!」之後,陳克治夫婦與飾演他們的年輕演員交頭接耳:「當年其實無嗌得咁大聲(當時沒有喊得那樣大聲)。」記憶與史實,哪個是虛,哪個才是真實?

六七暴動與2019年的「少年」對談
劇組找到2019年被告暴動罪的青年,演1967年紅色少年楊向杰,楊在左校製作文宣被拘捕,在英籍警官面前堅持愛國無罪,在法庭堅決不認罪,最終入獄收場。暴動青年在鏡頭外逐字讀劇本,不期然覺得:「印一張文宣就要坐監」是不公義的,導演再問他是甚麼人,鏡外的他堅定不移:我係香港人。兩代人的不公義重疊起來,就像一場跨代的身份與公義辯論。
找素人演1989年的林耀強,演1973年的陳克治,陳梓桓說要凝視的並不是演技。「他們的演技好差,但好有層次。看他們演出,已經不是在意他們『在演』戲,而是看他們perform(表現)自己,我覺得這個是很有趣的,突然間為這個重演添上很深的層次。」橫跨世代的情緒,我們在大螢幕看到不是一個時代的呈現,演員簡單一句「我不認罪」的對白,2019年背上暴動罪的青年表演的,其實都是自己。

重演歷史,成為《憂鬱之島》的戲碼。方仲賢演1989年的林耀強,感受當時的國族情懷後,方仲賢對當時的身份不同意,但對1989的香港人多了一份理解。隨着自由民主在天安門終結,港人的身份在六四之後漸漸產生改變,這個漸,是不知不覺間發生的。《憂鬱之島》正好抓着2020年維園的聲浪,高低起伏又充滿違和感的口號,喊出兩代人的身份認同。
「不論是89年的小強(林耀強)、六七暴動 ,或者追求香港獨立的年輕人,對於香港人的身份有一種好強烈的看法。百多年來香港人無辦法決定自己的命運,每個世代的身份認同也不一樣,但同樣有一種情緒,因為香港是一個不能決定自己命運的地方。」陳梓桓帶觀眾走進歷史長廊,終點卻只有一個,一個不能自主的困境。
1967與2019年的交接點,陳梓桓選擇用監獄作為場景,安排1967年少年犯楊向杰在監牢與2019年暴動少年對話,兩代「少年」同處一個「監牢」,那裏再沒有政治顏色,身穿啡色囚衣,四面是灰灰的牆。楊向杰聽了2019年少年的心聲,輕輕呼出一句:「我哋香港人,有冇任何時間,可以主宰我哋嘅命運⋯⋯?」二人各說各話,殊途同歸,最終走不出「憂鬱」的精神困局。

以他們的臉孔作休止符
走過混沌的1967、1973與1989年,《憂鬱之島》要為今日的香港下一個休止符,難度甚高。2020年陳梓桓仍走到現場拍攝,當時香港正處於一個「十字路口」,期間突如其來殺出《港區國安法》,接着是港人移民潮,香港重回「流動」的狀態。陳梓桓選擇以2014年佔中九子案鍾耀華的陳情書,以及40、50張即將入獄的面孔,作為2020年「分水嶺」的小結。這就像離散之前來一次大聚合,一切盡在不言中,「有些觀眾說,在影片中不止流露憂鬱的情緒,從中看到少少希望,當面孔拼在一起,雖然大家身處不同地方,面對很多不同的困難,但大家都是在一起的。」

《憂鬱之島》由2020年開始,花了15個月剪接,期間發生12港人、47人民主派初選案及《蘋果日報》被取締事件。陳梓桓說,2020年之後的歷史一再重疊下去,實在難以取捨,最後他還是「斷捨離」很多場景。12港人的鹽田港,2020年黎智英出席六四燭光晚會以及林耀強到岑建勳家作客食飯等場景,陳梓桓也狠狠剪走。這一次陳梓桓覺得,今次比2014年更客觀、更抽離去說故事,對於這份「冷靜」,亦曾感到疑惑。
「剪接的時候,我在問自己,那種距離並不代表我不在乎,經歷了2019、2020之後,我將焦點放在如何完結這作品,如何繼續講故事,在這個時代情緒好容易被牽動,好痛苦⋯⋯,但(完成作品)要function到好緊要。」
陳梓桓仍然惦記「智者婆婆」一言:「愈平靜的河是最深的部分」,在憂鬱之島說故事,首先疏理情緒,抽離一點,方能在深邃、流動的河流感受它的形態。

為作品找一條路
《憂鬱之島》率先在日本上映,緊隨其後在其他國家線上上映,對於香港電影這種新的發行方式,陳梓桓自言樂觀。雖然目前香港某些作品不能在香港上映,陳認為這樣反而令未來的創作更自由,有更大可能性:「年輕一代沒有fantasy(幻想)進入戲院的時候,其實是free(解放)了自己的創作精神,從前你想像入戲院放映,無論是商業操作,或是電檢處審查、國安法,其實是不斷在扭轉你的片去成為大眾主流,但當你沒打算在香港上映,那種創作、說故事的方法便可以實現,我覺得反而是一件好事。」

陳梓桓認為香港不乏電影人才,只是創作種類繁多,例如香港電影又細分「首部劇情片」、商業或獨立製作等,他覺得年輕電影人遊走於各個界別之間,最大問題源自於一種「迷失」:「在這個圈不知會去哪裏,反而失去一個好determined(堅定)的方向。」,他認為首先要訂下一個目標,便無論如何都會完成到。
除了清晰的目標外,資金亦是電影創作不可或缺的部分。陳梓桓指《憂鬱之島》曾獲得少部分本地資金,但現時已經完全沒有,後來獲得日本資金支持,在日本上映,未來或有計劃在其他國家上映,他形容新人可以將作品「面向全世界」,並參考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電影製作人,當地未必有一個發展健全的電影工業,但創作人依然拍到屬於自己的電影。陳梓桓建議年輕一代應主動尋找機會和出路,惟他再次強調決心的重要性:「釜山(國際電影節)可以是一個『跳板』,跳落去歐洲,找一些合拍模式,自己要找一條路,更加重要的是一個好肯定的決心,否則好快就覺得不夠支援,就拍不到。」

雖然《憂鬱之島》暫時沒有在香港上映,亦有不少同類型的香港電影被視為「非主流」,陳梓桓相信「這個年代有好多睇片的方法,甚至飛去日本、台灣睇都得。」
陳梓桓放眼國際,希望創作可以少一分顧忌,在「框架」以外如實記錄這座憂鬱之島,「在這個狀態下,我相信拍得成的作品都是好的作品。」
「陳梓桓,你都入鏡啦」,《亂世備忘》一名受訪者曾邀請他入鏡,那一刻陳梓桓真的入鏡,坐在草地訴說感受,記載了他的青蔥歲月。陳梓桓透露,下一齣作品,嘗試替自己解鎖,將自己放入鏡頭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