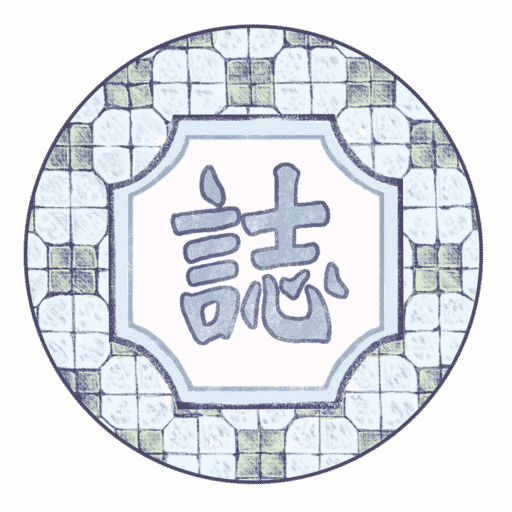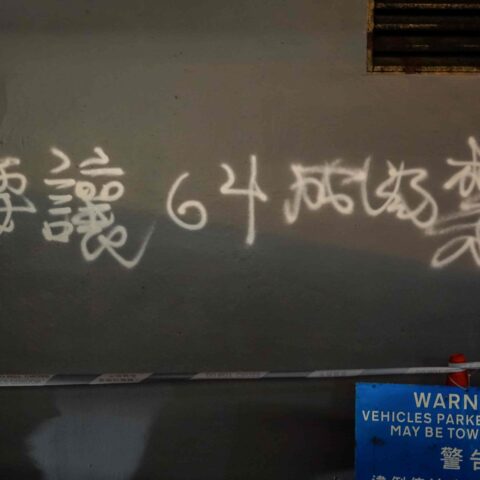「學民」一詞來自我們本有學生的身份,亦同時帶有世界公民、中國國民和香港巿民的身份,故此必須參與政策諮詢;「思潮」一詞則來自五四運動,當年學生撇棄中國舊有傳統思想,追求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渴望民主、思想和言論自由。「我們一班學生決意以當年的學生運動為榜樣,追求自由開放的思想自由,而非洗腦式的盲目愛國情懷。」
“學生運動,無畏無懼” 一群眾學生帶著理念,組成了學民思潮。 學民思潮的浪潮曾經席捲香港,由中學生牽頭發起的反國教運動在社會,也育成了不少名字讓人朗朗上口的學運領袖。 有人說,學民思潮是一個時代的傳奇。

學民思潮對你來說是甚麼?
「一個過程?….不同的可能性?…一個理想國?」
鍾禮謙在不足五百呎的議員辦事處辦公室內沈默了半响,反覆思量著,重組每一個在學民思潮的點滴。
專訪前學民思潮秘書處主席 鍾禮謙
鍾禮謙是兼「馬鞍山守護線」的成員,2019年當選沙田區(馬鞍山市中心)區議員。他曾經是學民思潮秘書處的主席,黃之鋒在區議會選舉中也曾他站台。
他在家中的衣櫃翻出九件學民思潮不同時期的T恤,娓娓道來每件背後的代表的學民年代和象徵的意思。筆者做了數個前成員的訪問,不禁驚嘆有人如此誠心地把這些「文物」都收藏得極為妥當。
「穿着學民的T恤,就唔好講粗口啦,唔好食煙,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大家很有共識,要合乎外界對於學生的想像。」
T恤背後,是一個鍾禮謙難忘的學生形象工程。
最後一批「成員」
初嚐熱血的學生運動
2012年六月,鍾禮謙剛考完文憑試,隨學民思潮的大隊出席六四晚會後,也參與了接續的中學生論壇,回家就填好網上的表格,決定加入學民思潮。「有青年民主黨,公民黨青年支部,都不是一些獨立營運的組織,見到有學民思潮,反國教議題適合、成員與自己年紀相若,就加入了。」
在學民思潮會議上提出意見都是年紀比較小的人。沒有輩份之分,反而有組織年資之分,較年長的鍾禮謙聽著比自己年紀小的黃之鋒和林朗彥等人的發表意見,亦十分樂意。
七一大遊行,本來終點是政府總部。學民思潮就呼籲群眾遊行到中聯辦,表達反對國民教育的訴求。「這其實這是一件很激進的事情,因為在2012年,除了社民連和四五行動,不會有團體因為本地的議題所以去中聯辦 。」學民思潮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創造出不同的可能性。這種社運的激情延續到擺街站、派單張,一班學生就這樣拖著一輛「買餸車」和大聲公就去表達訴求、做議題倡議。729反洗腦萬人大遊行後,中學生都盼加入學民思潮,成員人數一下子膨脹起來。
鍾禮謙憶述,組織內部「畫了一條線」,在某個時間點加入的人就是「義工」,而不是學民思潮的「成員」,而他自己剛好就趕上最後一批次,成為了學民思潮第一批的「成員」。

滿足社會對學生想像
解決政治潔癖的
組織的人數越多,意味著越難管理。「曾經有人說過是否要弄一個紀律委員會,穿着學民的T恤,就不可以做什麼的規矩。」雖然委員會並沒有成真,但此意見提出必有因。鍾禮謙坦言當時要死守社會對學生形象是怕被政黨騎劫。
「經常說政治很黑暗的,但學生是保持赤子之心,都是滿足社會對於學生的想像,所以很刻意地和政黨保持距離。」
現在回想其實一個挺有趣的想法,但是放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去看其實合理,「當時有些人會覺得連長毛都太激進」。

2012年九月一日,在學民思潮成功佔領公民廣場後,舉辦了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舉辦「良心話事 守護孩子」公民教育開學禮大會。台上有精彩絕倫的演講和群星拱照的演唱,台下一陣又一陣的歡呼聲,彷如嘉年華會。鍾禮謙當日被分派左糾察的工作,負責人流管制。他站在在通往政府總部的夏慤道天橋上,人流源源不絕,由集會開始都集會結束,「人潮一直向政府總部方向走」。不少年長的叔叔姨姨走過來拍拍他的肩膀,堅定地說:「後生仔加油」。
「那次是將事情包裝得很合家歡,國民教育明明就是很政治化的議題,但那天你就偏偏見不到有傳統政黨、政治人物在場,議題的話語權根本不在政黨。」
學民思潮行動升級
仍有放不下的學生包袱
未到佔領公民廣場行動完結,鍾禮謙就去了德國交流,一去就大半年。他在寄宿家庭體驗何謂將政治融入生活,開啟了他對「國民教育」的想像。
「德國人不會覺得政治是需要保持距離,沒有潔癖,做政黨之友很common (普遍)。寄宿家庭中沒有經歷過二戰,依然對納粹德國feel sorry、中學的field trip都會去波蘭的集中營去看,在香港反完國教,就在德國體驗好的國民教育如何提醒歷史不會再次發生。」

放眼世界後回港,即將升讀大學的他,仍繼續投入學民思潮的運作,甚至「越踩越深」。事隔一段日子,學民思潮已飽歷滄桑。組織基地從富德樓搬到荔枝角、佔領後有退會潮、也有不少新人加入、人事關係亦變得複雜。他形容,那時的學民思潮「好似經歷完一種很混沌的狀態」。
學民思潮繼續運作,歷史的巨輪繼續推進。 2013年3月,戴耀廷、陳健民與朱耀明發起「佔領中環」運動,學民思潮以率先主推「公民提名」的政改方案參與其中。學民思潮正式轉向關注「政改」議題,亦多次追擊官員要求政府回應。
「2012年去追擊吳克儉,兜完條走火梯,閘唔住吳克儉,都叫做影到交信相,但是去到2013年,已經不會再有這支歌仔唱。不會讓你再接觸到官員,就算連show都唔肯去做。」
2013年年底,學民思潮趁時任特首梁振英到沙田出席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地區諮詢會時,衝擊警方防線及拉扯警方鐵馬。「那一次有一點掙脫了學生很乖的想像,搶警察的鐵馬,一路拆鐵馬搬去後面,警察就一路拿新的鐵馬圍,接著警察都沒有鐵馬可以,那我們就用七層人牆地圍著他們。」
這些畫面在他的腦海重新上演,他雖同意學民思潮有必要升級,但卻一直思考如何行動之餘可以配合社會對學生的想像。 「我和核心成員沒有家庭包袱,但平時開完會食飯,傾偈都會聽到其他成員的家人可能都有些意見,總是有學生包袱 。」
罷課都有家長信
維持學生可負擔的抗爭成本
2014年4月,政改討論白熱化,學民思潮以及學聯提出學界別方案,包括在行政長官選舉中,必須要有公民提名,以及在立法會選舉中廢除功能組別等。
鍾禮謙強調,學民思潮一直與佔中三子和其他政黨保持距離,一直沒有明言會否參與佔領中環的行動。七月一日晚上的遊行的預演佔中,學民思潮都沒有參與,反而是同步發起「包圍特首辦」的行動 。「因為覺得佔中太溫和,所以不認同,當時甚至有個想法是甚至乎是想『夾實』佔中。」
直至所有方案被都北京人大得831框架摒棄,學民思潮與學聯先發動了學界罷課。「罷課其實是想keep話語權在學生,也許是有少少對政黨和佔中三子有一種抗衡。學聯就搞大專罷課,學民就搞了一個一日的中學生罷課,那時候都是在配合大眾對於中學生的想像,還有草擬了一封家長信。」
為了社會對中學生定型,學民思潮再次下了點功夫。 「最初大專學生罷課每天都有行動,但保持中學生的形象,也不令到抗爭成本這麼高,或令到社會或學生對於這件事情卻步,所以那時講明不想在中學生罷課之後有後續的。」
未解決的遺憾
彷彿失信於家長和教師

事實上,後續行動還是發生了。
「最後發生了,因為…….我到這一刻還是很struggle(掙扎)。」
總是對答如流的鍾禮謙突然支吾而對。 他說,罷課的最後一晚,除了學生,還有很多公眾人士到場。「那天晚上,大家都想 keep住(保著)民意。」那是2014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晚上。
他坦言,但是內部構想過一個廣場式的佔領,重演2012年的佔領行動。他們以為公民廣場的大閘會長開,有些人會睡在公民廣場,有些人會睡在添美道出面。」但是,他們萬萬沒有想得到「門常開」竟然關上了大門 。
他說:「那時一個很倉猝的決定。」
當日下午五、六點的時間,都來不及開一個正式的會議,誰在場就一起商討,做決策的是比較核心的成員。事隔多年,因為當時的慌亂,記憶已經變得很零碎,他早已忘記商討事宜的過程、只是記得數個關鍵的步驟:學民學聯的會議、問「有沒有人做死士?有沒有人配合?」,然後歷史就上演了。
黃之鋒突然號召「重奪公民廣場」,他們越過重重的保安、爬上圍欄,逾百人就這樣闖入公民廣場。「我掙扎是因為我是看重承諾的人,那些家長……肯放手去簽那個罷課同意書….我很肯定內部有說過不會有後續。」他側一側頭,嘆了一大口氣。
「我覺得那天無論什麼結果也好,都是打破了家長和老師肯放手讓學生參與罷課的承諾。」
從雨傘開始到拆大台
學民思潮都是「橋樑」
「重奪公民廣場」後,戴耀廷宣布佔領中環正式啟動。 數天後,警方發射催淚煙清場,惹來社會反彈,佔領區延伸至銅鑼灣、旺角等。 學民思潮也正式在金鐘佔領區「打躉」。「我們很堅持黃之鋒、周庭和黃子悅要盡量在佔領區訓,不要上立法會,頂唔順就回家訓。因為就算是學聯和其他政黨,晚上都有在立法會內訓,但是我們覺得要面對群眾就要身在現場。」
學民的成員在現場認識了不少參與佔領的人,不斷思考行動決策中「是否可以容納更多人的意見」。鍾禮謙,雨傘起初只有三方平台,包括「民主派政黨」、「佔中三子」和「學界」,學民思潮後來就提出要納入防線和物資組等人得想法,後來就改組了五方平台,讓「防線組」加入溝通平台。
對鍾禮謙來說,學民思潮直至雨傘運動完結,一直都在扮演「橋樑」的角色。
「第一,學民思潮可以是有政治有潔癖的大眾和社會運動的橋樑,大眾覺得學生做事最純真,會道德感召到一班不理會政治的人。第二,各個政治光譜中間嘅橋樑,當時未有一個很實在的本土派,但是起碼傳統政黨、傳統社運圈子,都不會對學民有敵意。 」
沒人想充當劊子手
學民完成歷史任務
這個角色隨著政改議題的討論空間幻滅漸漸淡化。本土派與泛民主派分裂,不少本地議題左右翼都有不同立場。 學民思潮的最後一段時光,成員各自關心著自己關心的議題,經營著刊物《破折號》及其網台。 他形容,這是學民思潮「百花齊放」的日子。
「2016年本土派和傳統政黨嚴重的交惡,但是學民是兩邊都有偈傾。我想,到現在都未曾有一個組織光譜的包容度可以那麼大,不論是對內還是對外。」
直至學民思潮結束,大家另覓新出路。常委們接受媒體訪問,作為時任學民思潮秘書長的他被問及學民思潮的結束,大家都說是學生包袱問題、左右路線問題、內部分歧問題…多年後,他得出了另一個答案。
「沒有人夠膽下決定學民思潮何去何從,任何一個決定都會有本土派或者左翼離開,但是學民的存在是超越這兩件事,就算開會開到臉紅耳赤都好,大家都會一齊打機,學民的人是超越工作的關係,。」
「沒有人想做這個劊子手。」
鍾禮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