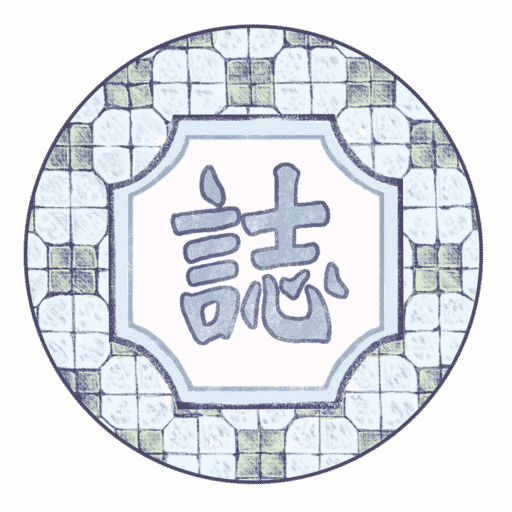在<衣櫃圍牆>兩篇文章,分別講述了男同志 Cody 以及跨女 Jessie 的故事。二人都患有精神疾病,而且都是慢性病患者。
是巧合嗎?當然不是。
早於2003年,流行精神病學家及性傾向法律專家 Ilan H. Meyer 已觀察到性/別小眾群體與主流之間的健康差異,建構出「小眾壓力模型」(Minority Stress Model),針對性/別小眾群體進行廣泛研究,發現他們因為長期承受獨有壓力,患上精神疾病的機會較異性戀者高2.5倍。
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於2018年發表的《LGBT社群心理健康研究報告》亦指出,「每三個 LGBT+ 受訪者就有接近一人出現中度或嚴重程度的抑鬱症狀,較香港公眾人士報告的百分比多出一倍以上」。
什麼是小眾壓力?壓力如何影響生理及心理健康?解決問題的良方又是什麼?性/別小眾友善的輔導工作者曾子正從自身經歷出發,綜合多年前線經驗,發現創傷心理治療可能就是那一帖解藥。他最近獲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錄取為哲學博士研究生,正在籌備本土研究,制定介入方式,招募志願者參加實驗,期望為香港的性/別小眾發展一套基於科學驗證的治療方案。
小眾身分交叉 壓力滾雪球
小眾面對的壓力分為兩大類,一種是外在壓力,另一種是內在壓力,都是因為其小眾身分而產生。外在壓力包括異性戀常規性、制度歧視、污名、偏見、社會孤立、排斥及暴力。生活在不安全的環境之下,一個人會不斷用外在目光審視自己,產生內在壓力,包括隱藏小眾身分、預期被拒絕帶來的不安,以及內化恐同等。
「性/別小眾不一定會發展至內化恐同,但是輔導者需要具備相關知識,才能進一步分析。」曾子正解釋,有些性/別小眾未必對自己的性傾向或性別認同感到厭惡,只是擔心別人拒絕。然而,有時也可能因為已經內化,事主也未必發現到內心深處的自我否定,「有人可能覺得自己好差,憎恨自己,但是自己也不知道,自然不懂得說出來」。
無論是Cody還是Jessie,他們在成長過程已經要面對家庭的壓力,以及同學的欺凌。投身社會工作之後,Cody會擔心別人發現自己的性傾向,Jessie則擔心別人發現她的性別不安。例如Jessie是以男性身分在家庭、教會以及公司生活,需要在特定環境才會以女性身分示人,正正是一種自我審視,擔心外界拒絕而引起不安,隱藏跨性別身分其實對她的心理構成長期的內在壓力。
美國學者 Mark L. Hatzenbuehler 研究精神病理學,他指出過度的壓力會導致負面思想、無望感、自我形象低落、情緒失衡、社交迴避等狀況,令身體功能失調。任何人只要長期承受過量的壓力,除了精神健康會出現問題,增加自殺風險,亦會累積成生理疾病,例如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免疫系統失調等。此外,受壓人士會更容易出現高危行為,例如濫用藥物、發生高風險性行為,較易感染性病及愛滋病。
近代增加了一個研究面向,就是小眾身分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以 Cody 為例,他是男同志,也是精神病患者,家人、同學、老師都不接納他的性傾向,精神病院的醫護人員在言語上又有所歧視,加上工作環境不太友善,Cody 無論作為兒子、學生、病人還是員工,在各種身分都要面對歧視和壓力,在滾雪球的效應下,生理及心理狀況因此愈來愈差。
躲進幻想世界
「我也是多重身分交叉之下的壓力成長。」曾子正說,自有記憶以來,他最記得的情緒就是恐懼。
「你冇用㗎!」爸爸話音剛落,曾子正的後腦就感受到一把掌。
「連少少功課都做不好!」每一把掌,每一句說話,都在攻擊孩子的自尊。
「爸爸……患有人格障礙。」曾子正陷入回憶之中,「他有太多控制不了的情緒,每一次爆發都會伴隨恐嚇行為。」例如他不喜歡妻子帶孩子們出街,每一次他們外出後,回家打開大門就是一片狼藉。
杯碟、擺設,甚至是三兄弟的玩具,可以打爛的都會被打爛。
有時,父親可能會威脅要跳樓,有時,父親可能會揮舞菜刀洩憤。
「自有記憶以來,即是幾時開始?」記者問
「幼稚園吧。」曾子正苦笑:「我會形容自己的童年是一片混亂:屋企亂、學校亂、性別認同也亂。」
由於天生五官標緻,身型瘦弱,曾子正在幼稚園開始已經常被誤認為女生。無論是稱讚抑或取笑,兩者都令他感到困惑。然而,家庭暴力令他變得膽小怕事,不懂為自己解釋。「我對自己的性別感到困惑,亦覺得別人認為我古怪,但是無方法改變局面,令我愈來愈沮喪。」
升上小學,曾子正開始感受到自己與其他男生不同,覺得自己格格不入。他不會踢球,也不會打籃球,每逢體育堂就站在一旁。他不喜歡男生們粗魯,男生們也看不起他瘦弱驚青。加上因為搬屋在六年之間轉換三間小學,曾子正難以與同齡孩子建立社交關係。

直到升上中學,曾子正才第一次過比較穩定的校園生活。他依然不會與其他男生一起踢波打籃球,但是他們也不會覺得他奇怪。「我很幸運,當時認識到一班好朋友,可說是保護了我,未有陷入嚴重的情緒疾患。」
自中學開始,曾子正的朋友就是小說。慢慢地,他開始在腦海虛構出多個角色,他們會在金庸的武俠世界以及衛斯理的科幻世界之中穿梭,演出子正為他們安排的戲份。「我會形容自己 log in 了《刀劍神域》。」返放學的路上,小息午膳的空檔,每逢可以放空的時間,曾子正就會 log in 腦海之中的虛擬世界,與其他角色四處闖蕩。
以前沒有專業知識,曾子正以為自己只是愛發白日夢,今時今日回看,其實當時已經出現解離的症狀。「這是自我保護機制,的確起到一點作用,不然我只會停留在家庭困獸鬥,很可能會發瘋。」他說。
不幸地,曾子正未能原校升讀高中,轉校後遭遇欺凌,又被取笑為「乸型」。他再次陷入自我隔離的狀態,應對方法只剩下努力讀書,全副心機投放在高考上。「我知道要考到入大學,不然我不會有能力拯救自己。」
創傷治療 擴闊身心容納之窗
成功考入香港大學之後,曾子正讀了一年教育,發覺自己不適合,毅然轉讀社工系。畢業後,他一直在輔導及心理治療的範疇進修,碩士也選讀家庭社會工作,「一切都是為了理解自己,想找方法幫到自己。」
家庭治療從原生家庭入手,解釋父母的一言一行對孩子的影響。「的確在某程度上幫到我,但是我依然不明白為什麼自己的情緒這麼容易起伏,處理人際關係永遠都若即若離。到底為什麼我會對某些情況感到害怕?」曾子正說。
幾年前,他在工作上的訓練課程接觸到創傷理論,覺得每一句都說到他的心坎,甚至總結了大部分性/別小眾的成長經歷。
創傷理論是基於近代的腦神經科學及生物基礎研究整合而成,研究發現創傷會影響腦神經,導致腦分泌失衡,繼而令身心及情緒調節的功能失調,在社交上出現適應障礙,處理人際及親密關係就會觸礁。
事緣研究人員發現成年人的創傷,絕大部分緣於負面童年經驗(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在成長過程,孩子長期及重複面對超越自身承受能力的壓力或經驗,逐漸會形成發展創傷(Developmental Trauma),再隨著時日沿負向軌跡(negative health trajectory)演變成複雜創傷(Complex Trauma)。
「一個人經歷創傷後,身邊沒有人支援,這個人為免再受傷害,就會不再信任其他人,結果只會一直處於不穩定的狀態。」曾子正解釋。
美國精神科醫生 Dan Siegel 提出「身心容納之窗」(Window of Tolerance)的概念,指出每人的情緒都有一個自動調節的範圍,只要情緒在可容納的範圍內起伏,基本上都可以自行調節。
然而,假如一個人的自我調節功能受創傷影響,身心容納之窗的範圍就會收窄,戒備機制會變得極度敏感。長此下來,即使面對中性的人事物,都會引起過高或過低反應,以戰鬥(Fight)、逃跑(Flight)或僵住(Freeze)的方式應對,跌入惡性循環,甚至抽離現實。
既然已經知道前因後果,為什麼一般的談話式心理治療不能改變以上情況呢?
首先,我們要了解大腦傳送訊息的方法。第一種是由上而下,經大腦發號司令,控制身體;另一種是由下而上,身體接收外界訊息後傳送回大腦。
談話式的心理治療,只是從上而下出發,由認知層面改變想法。問題是,當一個人跌入戰鬥、逃跑或解離狀態時,身體傳送的訊息會淹沒大腦。「當你因為緊張而心跳加速,呼吸短促,身體訊息會令大腦以為你處於不安全的處境。大腦只會立即進入戒備狀態,根本不會有能力思考。」
創傷理論延伸的治療方法,就是從身體感知入手。假如一個人發現身體開始發出危險訊號,先要學懂放鬆下來,例如深呼吸或者安住自己,讓身體經歷到安全感,重新發送訊號,大腦才會懂得思考。
「學習創傷理論之後,我也徹底改變了輔導方式。」曾子正因為工作需要,經常到學校開會,協助老師處理學生的行為問題。有一次,老師帶同一個學生與曾子正開會,他觀察到學生進門後已經目光遊離,三魂不見七魄。他第一時間走近學生,雙手搭在學生的肩膊。
「你怎麼了?我看你的肩膊都僵硬了。」他按摩學生雙肩,協助對方回到當下。
「你現在有沒有放鬆了一點?呼吸好像有順暢了,對吧?」看見學生的眼神開始集中,他知道學生已經從解離狀態慢慢回復過來。「同學,你先到外面坐一坐。」
關上門,曾子正轉向在座各位老師,「你們有留意到學生剛才的狀態嗎?」他們都面面相覷。
「許多老師和社工尚未接觸過創傷理論,面對類似情況,不是好言相勸就是處罰相逼,其實學生根本完全接收不到。」曾子正說。

聆聽身體 接收正面訊號
曾子正在前線輔導已有15年經驗,接觸過不少性/別小眾,發現絕大部分與自己一樣,都有不同程度的創傷。抱着助人自助的心態,他在工餘時間攻讀博士,希望以創傷理論為基礎,應用身體心理學制定一套介入方法,教育受過創傷的性/別小眾,協助他們及早脫離惡性循環。
第一步,事主先要學會聆聽身體發送的訊息。「受過創傷的人,通常不懂得感知自己的身體。」他解釋,例如事主自小就被虐打,長大後也不懂覺得痛,甚至不會流淚。「這是身體的自我保護機制。」輔導工作者可以透過冥想、呼吸、輕撫身體、自我擁抱等身體練習,協助事主建立感知及盛載能力。日後事主面對不安的情況,就會懂得分辨身體發放的訊號,透過同樣的練習協助自己放鬆,逐步脫離惡性循環。「身體心理學能夠協助事主建立心理韌性,身心容納之窗就會慢慢擴闊。慢慢地,就算日後面對更大的情緒起伏,事主也能夠自我調節。」
除了從身體出發改變大腦的神經活動,曾子正的論文導師莊兆鈞博士也在研究方法,協助事主在不完美的環境中,領會與同志身分有關的正面經驗(positive identity-salient experiences)。
現今社會整體對性/別小眾比以前友善,部分性/別小眾卻可能較難察覺到,也未必享受到這一小進步。
「一個人在成長過程內化了太多負面經驗,就算遇上正面經驗,也不懂得接收身體發放的正面訊號。」莊兆鈞解釋,例如看見同志友善的事物,心中會有喜悅,面部可能會有笑容,但是有些性/別小眾反而會觸及一些舊傷口,或因過往未有機會被善待而悲從中來,頓感失落。
假如有方法協助性/別小眾分辨過去的傷害是如何觸發自我防衛機制,再教導他們領會正面經驗,就可以擴闊固有認知,提升整體的身心健康。
簡而言之,就是一邊清理大腦的垃圾,一邊為大腦輸入養分,從身體及認知雙管齊下。

「有一段回憶,事隔多年我仍然清楚記得。」那時,曾子正仍然是小孩,因家中的動盪而焦慮不安,父母的一位朋友溫柔地擁他入懷。感受着對方的呼吸節奏和體溫,大腦和身體本來已經在跳動的過敏神經,隨着姨姨平和的心跳,逐漸安定下來。「那份安全感,一直儲存在我身體的記憶。」
很多年來,曾子正與人相處都是比較自我封閉,近兩年學習創傷理論後,終於找到最後一塊拼圖,重新認識自己之餘,也重新與世界連結,他坦言對此仍然感到有點陌生。「我會形容自己現時身處一個舒適圈。圈內有不同人,與我有不同距離,我可以自由地選擇親近或走遠。」他說:「這些人都是確確實實存在於現實生活,我不再需要虛構角色陪伴,也不再需要走入幻想世界才覺得安全。」
遇怪魔,不用即刻變大個,只要願意變大個,懂得變大個,一切都會慢慢好起來。
採訪/ 伍詠欣、 黎𧘲妤
攝影/ 黎𧘲妤
編輯/ 關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