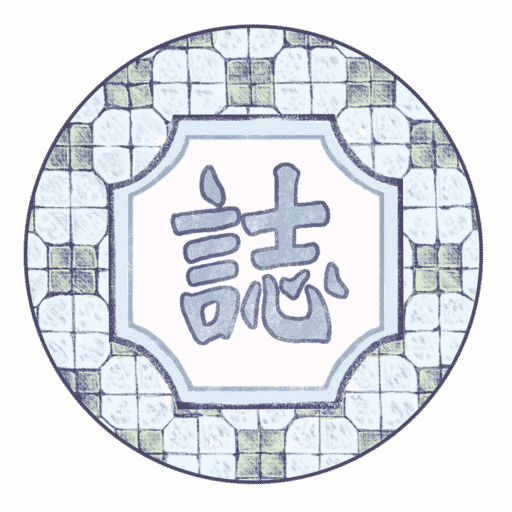在香港戲院獲准上映,還是被禁上映,是「天堂」與「地獄」的結果。能否上映,是一齣電影在螢幕上生命的Opening,也可能是它的結局。香港電影的現況是,可能到上映最後一刻才被揭盎。
今年第16屆鮮浪潮「委曲求全還是逆命而行」(to Live or to Fight )系列的兩部短片──《群鼠》與《Time, and Time Again》,前者臨開場前獲取「核准證明書」;後者則不獲准上映,在信件中指明影片無法通過簡單的修改或刪除,以符合審批標準(詳見<禁片年代>王彥博訪問全文);信件亦清楚說明,今天處方檢視的,還有網上言論,紅線已蔓延至網絡每一個角落。
繼去年鮮浪潮短片《執屋》被禁,今年《Time, and Time Again》同樣難逃被禁厄運。《群鼠》導演兼編劇譚善揚、胡天朗說認為不論殺與被殺,也是命運共同體,沒有所謂「生還者」,「每一個人也像等待被人劏宰的老鼠,在這個制度下是無可避免的一個結局。」
既然「被人劏」是不可逆轉的結局,為何仍然拍電影?「與其說電影是諷刺,不如說這是一種呼喊」,譚與胡異口同聲說。一口呼喊聲,二人選擇了電影在這個時代留痕,拍電影的動機,其實可以如斯簡單直接。

Part I 權力與秩序
《群鼠》講述校園內一群恃勢凌人的風紀,以維持秩序之名,濫權為實,欺壓不順從他們的同學,即使被揭發在校內販賣大麻,甚至導致同學墮樓身亡,學校依然視而不見,達到無法無天之境。最後同學群起反抗,身為風紀之一的主角「變節」,仍改不了腐朽的制度。

《群鼠》中含有正面宰鼠、師生群毆的鏡頭,意識大膽。躁動年代引發對制度的反思,《群鼠》內種種畫面令人聯想到徐克1980年執導的三級電影《第一類型危險》1。《第一類型危險》有針刺老鼠、製造炸彈等毛骨悚然的鏡頭,結局更用上六七暴動的新聞相片作結,徐克在電影中流露對政權、歷史、身份認同的看法,比今日的導演更露骨、更大膽。
《第一類型危險》毫不忌諱的觸及「六七暴動」及港人排外心理。其中一幕,主角連當時的港督是誰都不清楚,似乎暗示港人對於身份認同的不確定性。不甘墮落的少年苦苦探尋生存的出路,最後他們於戲中的下場和死亡,象徵着一代人的無力感。
《群鼠》的故事背景,同樣發生在一個動盪浮躁的時代,兩部戲同樣被評為三級,《群鼠》與《第一類型危險》有一個共通點:影片流露出的精神,終究是離不開當下年青人的憤怒。
《群鼠》呈現一個權力嚴重失衡的制度,是一個怎樣的制度?
一開始為何會構思《群鼠》這個故事?
我們在想有什麼題材想拍, 一開始其實想不到,之後就開始想,究竟當時我們有甚麼情緒和感覺?後來我們說出了一些感受,想起了《城市與狗》這一本書,是秘魯作家寫的。
故事講述在一所像集中營的秘魯軍校中,學生們互相廝殺,那種被軍訓和廝殺的情況,好反映到我們當時想表達的情緒,某程度上是一種社會的縮影,便用了這個故事作為創作藍圖。
故事要從秘魯調整至切合香港的情況,所以不能用軍校,便選了我們最熟悉的學校。在一個有權力和秩序的地方,故事才能夠發生,這兩個元素便是故事的骨幹。
着眼在權力和秩序,是因為覺得很切合社會現況 ?
應該說是⋯⋯很符合我們當時不滿的狀況,是否貼合社會是因人而異的。我們想表達年青人的憤怒,或者對於制度的不滿。
片中的主角「煙仔」是風紀之一,似乎好人壞人都是他,為何會有這個角色設定?
我覺得這條問題挺有趣,我們一開始都討論了很久很久⋯⋯有想過煙仔會否真的太壞?有想過要不要令他善良一點,令觀眾可以更代入。即是⋯⋯這個人太仆街(混帳),到最後他做甚麼你都不會care。但後來我們堅持讓他徘徊在「善」與「惡」的邊緣,就是想讓觀眾覺得⋯⋯我想講咩呢⋯⋯(突然忘詞)
(笑)開場白那麼久⋯⋯我想說的其實就代表着我呢⋯⋯
即是⋯⋯我覺得在這個時代的開端,並不是絕對的「善」與「惡」,煙仔本身都有些「黑底」(黑化),然後嘗試去做一件正確的事?
想到一個punchline⋯⋯我們感興趣的,不是那種純正的「好人」或「正義者」,而是那種搖擺不定的人,這些人要如何在一個充滿罪惡的世界生存,做一個好人。這就是我們最初的命題:在一個如此邪惡的世界,如何能夠依然做一個好人。
究竟你走前一步做一個壞人,或是走前一步去反抗呢⋯⋯擇善固執。

結局是想營造一種諷刺的感覺嗎?
我覺得這個字好負面,與其說是諷刺,應該可以說是一種呼喊,我們知道被壓迫的。是有反抗,但制度不被改變,依然會有這個下場,即是很想再喚醒某種意識。
PartII 港英
自港英殖民時代至回歸以後,香港電影審查政策經歷多次變化,某程度上也反映政府在管治上的寬容度。在不同年代均有獨特的考慮,惟政治因素可說是古今通用的標準。在冷戰時期,港英政府特別關注社會的穩定性,以及在地緣政治上如何維持香港的「中立性」。 因此當時電影審查的標準主要圍繞着數項原則,包括會否令香港社會不穩、錯誤描繪香港關係、煽動種族與國族仇恨等等。
在上世紀50年代初,港英政府針對共產陣營的審查,特別戒慎來自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電影,而不是蘇聯電影。因當時的英國官員認為中國電影起用華人演員,並非白人,相對蘇聯電影會令港人較易投入和模仿劇情,更具顛覆性。(參考《冷戰光影:地緣政治下的香港電影審查史》 (2019) )

直至60年代,政府新聞處會派員到戲院視察觀眾反應,例如在1966年某日,官方派員到南洋戲院(灣仔摩理臣山道)與市民一起觀看《毛主席和百萬文化革命大軍在一起》,按照該人員的報告,戲院入座率不過一半,電影開始時只有零聲掌聲,官員從而推測當時的中國政治電影,並不受市民歡迎。港英政府用這種觀察方法,預測電影潛藏的政治力量。套用這個政府邏輯,假若座無虛席,掌聲如雷,便代表該齣電影有一定政治影響力。
現時的電影初檢,依然是由行政長官委任的檢查員小組負責,若檢查員認為影片違反《電影檢查條例》或《有關電影檢查的檢查員指引》的原則,他們會指明須刪剪的片段,或直接拒絕影片上映。若製作單位不服檢查員的決定,可「上訴」至審核委員會。但2021年6月新增的條文中提及,假如檢查員是基於「國家安全」作決定,「上訴」並不適用。
《Time, and time again》不獲上映後猶如石投大海,反觀電檢處在最後一刻放行《群鼠》,對於官方、甚至創作者來說,是否就像一場試探或賭博?檢查員在作出判斷時,是如何詮釋影片背後的思想型態?劃上紅線,是否能軟禁創作者及觀眾的思想?
《Time》不獲批上映,但《群鼠》能夠上映,你覺得官方是否想證明審查制度還保留一點自由並沒有禁絕所有聲音,有種「二選一」的意味?
我覺得本身審查這件事,不是說色情或暴力那一種, 而是政治審查呢,本身已經是不太對,就算它放行或者不放行,討論這件事本身已經是錯,我覺得藝術不應該受到政治審查。但「二選一」呢,我們又不覺得是陰謀,但我們依然是它手上的棋子,沒有話事權。即使我們過了審批,但《Time》過不到,我們一樣覺得好氣憤 ,因為我們是一個共同體。因為如果《Time》被禁播,便代表未來千千萬萬段片都有可能被禁播,一段片其實代表了全部人正在面對的處境,我覺得本身這件事就是荒謬。
我不太同意「二選一」這個說法⋯⋯我們一隻字都沒有提及政治,或者在社會發生過的事,但背後的意識和精神是相似的,可能是⋯⋯他們現階段還沒找到方法勒死我們?
我覺得本身要想「是否需要ban」,這件事是錯的,不是代表《Time》更加值得被ban。

但以前港英政府都有對電影做政治審查,甚至比現在更加嚴謹,若果完全不做政治審查,會不會是推翻(或忽視)了以前的歷史?
我覺得不是所有歷史都值得保留,如果是好的便保留,壞的便不要保留。藝術是講自由,令更多人說到想說的事,一定是比有限制好。例如有些外國的偽紀錄片,假扮有總統被刺殺成功,這件事很瘋狂,在香港應該不會發生這些事,但意思是說⋯⋯別人起碼有權利可以拍這些。
我們都知道政治審查不是2022年香港獨有的,中國、英美和東歐等國的電影,全都有政治審查。而往往好吹脹的是,我們經常覺得禁播的電影是最好看的⋯⋯
(笑)這句有點嘔心⋯⋯但我們沒有被禁播喎!
(笑)係喎⋯⋯總之重點是,這種禁播抹殺了許多創作人的心血,從古到今都是不公義的,所以不只是針對香港,例如伊朗有導演被囚禁,我們都好關注這些事,不公義是全球都有。而不是覺得⋯⋯以前都要審查啦,然後一齊鬥慘,我們不是鬥慘大會,要追求進步。
PartIII 港台
經歷近40年白色恐怖的台灣,戒嚴時期的國民黨奉行單一文化統治,打壓異見者之餘,亦不乏歌頌功德的政治電影,以及風花雪月的娛樂片。上世紀80年代初至1987年解嚴以後,在民主風氣下政權再擋不住創作人的思潮,挑戰社會禁忌的寫實題材,在一股「新浪潮」爆發出來。
回顧解嚴前後,台灣社會正在逐漸解禁,但有台灣電影龍頭地位之稱的「中國電影製片廠(中影)」,內部審查機制仍十分嚴格,除了片廠主管,國民黨亦會派員仔細審查每份電影計劃書,獲批後才能開拍。

為了突破「中影」保守的意識形態,當時仍為製作助理的小野和吳念真,選擇將計劃書寫成很有「創意」,以隱藏電影的真正意圖。例如《兒子的大玩偶》(1983),呈交給中影的計劃書說:電影宣揚國父孫中山的哲學思想。可是這部三段式影片的情節,卻處處刻劃了老百姓的困苦和堅韌。當中最後一部影片〈蘋果的滋味〉,觸及到60年代刻劃台灣對美國在軍事及經濟高度依賴的情況。影片遭保守派影評人攻擊,認為該片把台灣落後的一面赤裸裸地呈現出來。後來中影下令大幅修剪片段,幸好導演萬仁聯同製作團隊,利用輿論壓力向中影展開反擊,迫使它撤回修剪令,才使〈蘋果的滋味〉能以原片放映。

雖然1983年規定稍微放寬,電影無須再經政府新聞局事先審查,從《兒子的大玩偶》一事可以看出,比起官方審查,電影公司還是存在自我審查。《群鼠》的製作過程中,包括找演員和拍攝場地等,亦面對着各種的自我審查。背負著沉重的社會壓力,面對各界自劃紅線的無奈,創作者是否真的能毫無懼色,忠實的拍電影?
創作《群鼠》時的故事時,有沒有害怕一些情節會被禁?
我覺得在一個有點腐朽的環境下,這類人的存在是無可避免的,所以在現實找到一些相似的人是不出奇,這間學校不止代表現在香港發生的事,而是每一個秩序崩壞的地方都會出現。
如果創作的時候,你害怕,便很難說到你真的想說的東西,便不是由心而發的創作,會有好多考慮因素和顧慮,不能夠用作品說話。倒不如直接不要做,做得這樣虛偽的話。拍電影第一件事是要真誠, 觀眾會看到的,你怕的話觀眾都會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