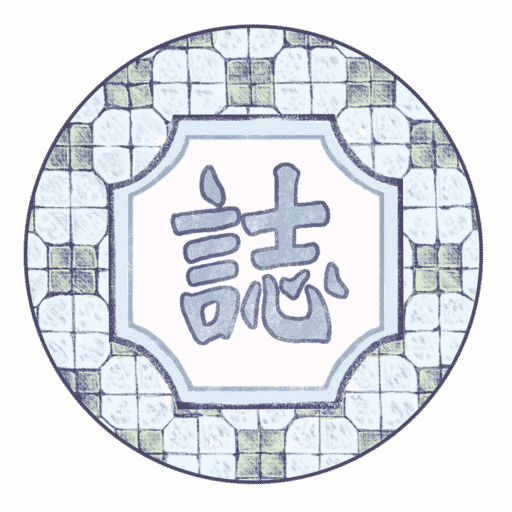據說,在我未出世的1989年五六月春夏之交,北京學運激起香港各區「開花」全港多區均有大遊行,屯門集會人數一度多達二萬五千人,是為屯門人的「威水史」。去年政府以防疫為由,六四維園晚會首度被禁,各區遍地開花,屯門公園為其中一個「據點」,逾五百人參與,約是1989年的2%,但燭光照亮公園人工池,場面墟冚,觸動人心。
港區《國安法》實施後,未到六四,建制媒體舖天蓋地消息指 「穿黑衣」、「叫口號」和「點燭光」均屬違法,「力勸」市民不要參與未經批准集結云云。民間悼念由維園到遍地開花,由各區要地轉移教堂。惟防疫政策下,教堂座位有限,塞不下的人,走到哪裏去了?
2021年六月四日,港島、九龍燭光處處,但去年屯門公園的盛況今年已不復見,我沿去年的路線重遊,途中幾乎變得鴉雀無聲,後來在人工池發現了第一點燭光,甚是意外。在沒有大台、沒有號召,回歸個人的悼念,又是怎樣?


去年約十名屯門區議員在屯門公園入口擺設街站,響應支聯會的網上集會(圖左);今年支聯會已沒有實體及網上集會,區議員甄霈霖在場派發蠟燭,多名警員在旁監視。
人雖凋零 一息尚存
「今日我們屯門區議員,響應支聯會的呼籲,遍地燭光悼六四。在屯門公園,八時正我們會透過螢幕直播支聯會網上集會,八點零九分,我們全香港將會默哀一分鐘,悼念六四的死難同胞⋯⋯」那是去年屯門區議員(屯門鄉郊)兼支聯會常委張錦雄,在屯門西鐵站外手持麥高風,大聲地說。背景聲是市民此起彼落地唱著「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著吧」,和不間斷的抗爭口號。人頭湧湧,屯門站四方八面都水洩不通。
一年後,六月四日,下午五時半,我看見張錦雄及另一屯門區議員(兆翠)甄霈霖,在同樣的地方,派發蠟燭,少了嗌咪的聲音,少了伸手接過蠟燭的市民,多了便衣警員,多了一部攝錄機,拍下張錦雄及甄霈霖的行為,二人派發蠟燭至六時半就離開了。
時間尚早,我入了屯門公園走一趟,沿途看見在閒坐的公園阿伯、跑步的人、買餸回家的師奶,盪韆鞦的小朋友,和在享受家庭樂的父母。世界如常轉動,如此氣氛,我怎樣都不覺得,今晚會有甚麼驚天動地,或是莊重嚴肅的事情,與此公園拉上關係。
在園內走了一轉,約六時半,我回到起點等待,守候我覺得會平淡無奇但期待會有點不一樣的時刻。下班的人一批批地路過,一批批地離開,沒有人有停下來的打算。


她叫 Louise,她認為悼念不一定局限於維園,有心記得的,到處都是可以悼念的地方,交談期間,她一直小心翼翼護著燭光。(劉愛霞攝)
沒有號召的悼念 卻有燭光亮起
晚上八時多,我沿去年的路線窺探園內光景。或許去年人太多,天氣酷熱,感覺由公園入口行到人工湖的路,走了很久很久,那時我還要停下來喝水稍竭一會才能繼續,如今卻很輕鬆,不到幾分鐘就來到了人工湖附近。我想過好幾個如園內沒甚麼發現,我會做甚麼的可能,但就未有想過,有市民早已到達人工湖,點起了一盞燭光,有人在長椅上擺放亮著的電子燈,有人亮起手機電筒。
我坐在遠處,看著有另一人走向那位點起燭光的女子,向她「借光」,她大方地分享,很快,旁邊多了一絲光。大家小心翼翼護著眼前的燭光,生怕手一離開,風一來,火就會滅。我厚著臉皮上前向該名女子搭訕,表明身分及因由,問及她選擇來屯門公園的原因。
一人點燭光的她叫Lousie,近40歲,育有一子一女的媽媽。Lousie 對六四印象很深刻,那年她小六,家裏的大人在打麻雀玩樂,小朋友只能在旁看電視。Louise 看著電視畫面播放著坦克車進入街道的畫面,她記得有人躺在地下,她說,當日電視頻繁地播放,整個新聞片段牢牢印在腦海裡。Lousie 驚慌得哭起上來,但她憶述大人對小朋友的哭,僅是「她哭了」的反應,更遑論是安慰或疏導情緒。
Louise 完全沒有想像過遙遠的他方會發生如此「死人」事件。那年之後,中學至大專期間,及至工作後的幾年,Louise 是維園的常客,屈指一算,她說去過維園六四晚會的次數有十五、六次,但她謙稱自己去的次數是「很少」。問其緣故,Lousie 解釋有時自己也會「懶惰」,或是婚後因要照顧小朋友而未有參與其中。
現時子女長大了,是日晚上女兒和朋友到了附近教堂彌撒,Louise 在公園內進行自己的一人悼念。她認為,悼念發生在同一個地方雖有感染力,但需要人走出來承擔壓力,如果沒人走出來,則未能凝聚起來。Louise 稱,如果每個人都有心,悼念不一定局限一個地方。
她說,「每個人都應該有個想法,你的初心在哪裏?你的初心是為了甚麼而繼續存留這個信念,令你每個時段,這個時間做一些活動,如果初心不變,我覺得(地方的)影響不大」。
屯門居民Louise

2020年六月四日進入屯門公園參與悼念的人潮如鯽。 
2021年六月四日通往屯門公園的大路,冷冷清清。(劉愛霞攝)
篡改歷史的時代 以口述承傳真相
昔日的大人在電視機前打麻雀,沒有告訴Louise 電視畫面是怎麼一回事,Louise 已為人母,子女是如何得知六四事件?她說要「多虧政權」的作為,才會令小朋友問起,Louise 一五一十將當時自己的經歷向子女說明,她說小時候小朋友未必聽懂,隨年紀增長,他們學校教育,如通識科會接觸到相關議題,如今子女十多歲了,Louise 女兒是主動提出要到教堂,說實話,Louise 坦言會擔心,但她以「習慣了」的口吻說,「就算不是跟他們(子女)同行,(我)會在另一個地方等他們,等待他們回來,我才會走,我永遠是做Backup(後備的角色)」。
但通識科都被易名「公民及社會發展科」及課程要改革,在教育整頓下,歷史及記憶要如何承傳?Louise 有樂觀的心態,說「通識科可能沒了,可是我們人未死。(就算)我們這群人可能會死,但他們(下一代)仍然在⋯⋯我們可以教下一代⋯⋯或者香港的書去到外國,那都是知識。而知識不局限於書,可以口耳相傳,一代傳一代」。Louise 指,子女都有向Louise 取經,如何面對政權刪減歷史,或子女擔心新移民來港(國內文化)或會同化同輩。Louise 則教子女,「你也可以同化你的同伴,(每個人)傳給下一輩,各自努力」。
「忘不了的,就算政府做任何事,其實我們都忘不了。 事實歸事實,就算人如何長大都好,大家都會記得。是否你逼大家就會改口?其實(我)心裏記得所有事。我年紀這麼大了,都忘不了」。Louise 一直雙手護燭光,說話時十分感慨。


去年市民參與默哀儀式後,共同步行到園內的人工湖,手持燭光,叫喊抗爭口號,「圍爐取暖」;今年光景不再,湖邊有市民點起一盞小燭光,自行悼念。(劉愛霞攝)
警方夜襲截查 容不了餘光
與Louise 交談期間,獨自或結伴來到湖邊的人數增加至十餘人,大家都靜靜地坐在湖邊的石壆上,沒有昔日的叫喊或是高歌,但彼此共享着這個空間的不言而喻。後來,有一名騎着單車的男子,透過車尾音箱播放著 Beyond《十八》、《自由花》、《願榮光歸香港》及流行歌曲,音樂奏起時,聽懂的人都忍不住別過頭,去尋找這位有心人。Lousie 附近有幾位年輕人,言談之間隱若聽她們好像以宗教進行悼念儀式;另一邊廂聽見有人在「講故」,一名叔叔向幾個後生仔大談九七前後的面貌,還有一位上了年紀的伯伯,倚著燈柱,拿著燭光在旁靜觀。我很想上前與在湖邊的人談話,尤其是那位伯伯,但未能成事。
單車男發現公園內有二人疑似便衣人員,當場質詢對方,二人並沒有正面回應,場內氣氛開始緊張起來,有人大叫「手足,屋企張床隨時要人」。說時遲,那時快,大約晚上十時半,約三、四十名白衣、軍裝及便衣警員,突襲衝入屯門公園人工湖空地,警員「手指指」,其後從四方包圍及截查在場人士,包括我。

約晚上十時半,大批警員突襲衝入屯門公園,截查在場自行悼念的市民,很快,湖邊又變了無人之境,仿似這裏從沒發生過任何事。
警員要求我出示身分證及記者證,指接獲有人投訴有市民大叫「死黑警」及在場內生火,於是到場。我問這是否執法行動,及抄下的個人資料將會作什麼用途,警員沒正面回應,但指如案件涉及刑事調查,將會聯絡在場人士。我追問現時公園內的行動是否已涉及刑事案件,警員也沒正面回應,指需要調查,反問我有否在公園內生火。警員一出現,大部分民眾幾乎被嚇得雞飛狗走,擾攘一輪,場內幾乎一掃而空,仿似這裏從來沒事發生過。
湖內剩下燈柱燈罩的光,折射到水面的倒映,沒有了蠟燭,沒有了人。若果將來有人說,2021年6月4日,有市民在屯門公園內生火,我會否定這說法。那些光不是自私自利,用作烹飪或節日慶祝娛樂,那些光是屬於哀悼的。哀悼的是三十二年前在天安門死去的靈魂,還有今天身在公園內但未能暢所欲言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