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男性受害者Howard想起當年被導師WP侵犯的經過,多次求助不果,每一個組織就像一幅牆,此路不通,六年來他受盡煎熬。
據社會福利署2022年的統計資料,性暴力受害者人數共740人,女性佔96.2%,男性僅3.8%。服務資源亦按此比率的分配,令男受害者得不到合適的援助。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總幹事莊子慧指出,現時社會數字無法反映男性性暴力受害者的需求,官方求助數字處於低位,資源分配自然較少,成了一個「死胡同」。
「好像討論性暴力永遠就只有女性」
在走入警署報案前,Howard曾向組織求助,但始終找不到協助。被WP侵犯的一年後,Howard曾致電「明愛曉暉計劃」求助,電話一直無人接通;六年後他踏進警署前,曾鼓起勇氣致電為性侵受害者提供服務的「東華三院芷若園」,希望他們能陪同報案,惟電話三小時無人接聽,他只好自行入警署報案。
報案一刻,亦受盡傷害。首位接觸他的報案室警員質疑為何在六年後才報案,該警員初步了解案情後又以「咁又點」、「咁你想點」等口脗詢問他的來意,令他感到孤立無援。「我當時沒有報案,就感覺自己好像不是受害人似的,整個系統也在否定我,說我不是一個受害人,好像我就不值得這個司法系統、警察去幫我。」Howard說。
Howard坦言,他讀畢五年的法律學位,對司法的程序較熟悉,不太需要法律支援,但如果一個普通的受害者,他反問:「他們該怎樣處理?」。Howard之後找到風雨蘭,機構又好像有點愛莫能助,「好像討論性暴力永遠就只有女性,男性是不是不會受害的?」
他表示,明白相關機構資源短絀,但他認為男性性受害者的部份「被填黑」,不但無法取得適當的支援,連受害者的數字也無法得知,「我不肯定在700萬人當中,有多少人與我的經歷相約,我很想知道。」

組織承認男受害者資源不足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總幹事莊子慧接受《誌 HKFEATURE》訪問時表示,男性性暴力受害者服務的主要「死因」,在於男士的求助數量不多,未必能真正表達到社會需求或狀況。
莊子慧指出,現時法例上並無明確的用詞能代表男性被性侵,令男性更難以表露自己曾受性暴力對待。以《刑事罪行條例》第118條「強姦」為例,條文表明「任何男子強姦一名女子,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終身監禁」,亦即法例條文早已假設男性是加害者,女性是受害者。
她表示,法律對男性受害者的否定,再加上社會對於性別意識的匱乏,往往令男性的求助人數減少,「男性說性暴力這件事其實已經很困難,男性很多時候在社會上被假設是強者,怎樣跟別人說這件事?」她以女性受害人為例,她們求助也不是一件易事,社會對於性暴力受害者的目光,往往讓她們難以開口,遑論男性受害者。
另外,莊子慧表示,人們對於性暴力充滿迷思,而這種迷思對於男性而言更嚴重,「尤其是當男性受害人出來說,很多時候下面的回應會說:是否『益』了你(便宜了你),你那時候是否有身體反應等等。」
她舉例指出,男性受害人公開經歷後,有機會被有意無意地質疑,這些回應均為他們的求助築起一道圍牆。
父權社會下受害者更隱性
缺乏了反映男性受害狀況的真實數據,社會難以根據真實情況為受害者分發適切的資源。事實上,在網上搜尋到的男性性暴力支援服務寥寥可數,較為人知的服務就只有「明愛曉暉計劃」及「東華三院芷若園」。
莊子慧形容,這處境是個「死胡同」,「如果連數字都沒有或者反映不出來,一些擺放資源的人就會想、是不是Cost Effective(高成本效益),可能我們只有幾個個案,是否要開專門的服務給你呢?」
莊子慧又坦言,針對每個性別的受害者需要不同的服務計劃,這也是風雨蘭無法同時提供兩個性別的服務的原因。她表示,男性受害者與女性受害者的處理手法不一樣,社工或輔導員需要有足夠的性別認知,「(香港)始終是一個父權的社會,男性受害者要說出這件事時,他可能不希望自己被定義為一名弱者。」
她又指,過往有家暴服務提供者曾表示,男性多傾向在輔導期間去行山等戶外活動,而非像應對女性受助人般,只在房間内與他們一對一交談,「他們未必覺得是合適,或者他們覺得不舒服,他們已經不會來了,會影響他們真的去求助的意欲。」

分享經歷 冀增公眾關注度
「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就是你要去到一個絕望的狀況才會有人去關注。」莊子慧認為,要解決男性受害者服務不足的問題,要從傳媒方面入手,讓更多人對此有所關注,繼而表達對資源的需求。
她又認為,政府有責任在性暴力議題上投放更多研究資源,最基本需調查香港有多少人曾經歷過性暴力,才能有更多數據去研究解決方案。她表示,政府可參考澳洲研究兒童受虐的做法,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與受訪者進行深入交談,了解他們的經歷,讓社會有更多數據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更適設的服務。
Howard明白社會關注度會影響服務的多寡,因此他希望透過披露自己的事,讓社會對男性受害者的關注度提高,更希望能讓與他有相同經歷的男性知道自己並非孤身一人,「我坐不到時光機回到未被侵犯的時候,但至少這一年我不想再讓自己後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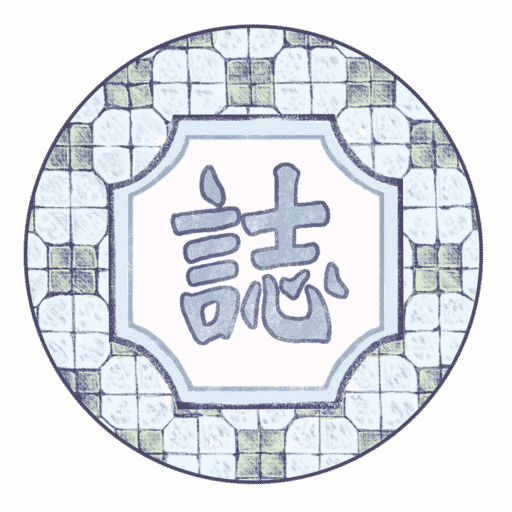






-1620x1080-1-480x480.jpg)






